不要畏懼不確定性,學會擁抱它。
各位好,昨天在我的知識星球上看到一位讀者的來信,這位讀者說:小西,我愛人在某跨國大企業做技術工程師,公司現在業務轉向,愛人面臨一個難題,要麼人隨事走,去美國。要麼繼續留在國內,慢慢被邊緣化,甚至被開掉。
我這位讀者於是很糾結,她不反對跟著愛人去美國,但擔心自己到了美國之後找不到工作,而家裡還有兩個孩子,萬一如此,到美國生活肯定會特別艱辛,不確定性太多。
但是如果留在國內,考慮到這幾年就業壓力飆升,她其實也沒有多少信心。
我這位讀者朋友很糾結,想聽聽我的建議。
考慮到有類似糾結的朋友挺多的,我決定寫一封長信統一回應之。首先說明,建議我不會隨便亂給,因為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但我想我可以提供一些「思維拐杖」,幫助朋友們做出自己的抉擇。
這位讀者朋友來信中提到了「不確定性太多」的這句話,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段子:
據說鐵達尼號剛剛撞冰山的時候,在短暫的衝擊之後,遊輪上的舞廳恢復了電力供應,人們在短暫的惶恐後並沒有逃散,而是歌照唱,舞照跳,覺得這不過是打斷宴會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直到船長下達了準備棄船的命令,大多數人才後知後覺的一鬨而散,只留下舞廳當中的樂手們出於職業精神一直演奏樂曲安撫人心,直到船隻沉沒。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呢?
根據事後媒體對當事者的採訪,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很多人仍本能的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鐵達尼號這艘船實在是太大了,是當時人類工業的奇蹟,這樣大的船還號稱「永不沉沒」,就給人們帶來了一種錯覺:那種海洋本來應該給渡海者帶來的危機感和不確定感,似乎已經被巨輪所取消掉了。相比之下,跳上救生筏這樣的小船反而是一種直面不確定性的選擇,所以很多人會本能的不選。
但我們今天知道,這其實是一個錯覺,不確定性就像熵增一樣,它只能夠被轉移而無法被取消。
像鐵達尼號這樣的巨輪,或與之相似的大體系,它們所起到的作用不是「取消」掉了船上乘客們的不確定性,而是把這種不確定性上推、集納了,這就一旦出現「黑天鵝」事件,不確定性衝破大體系的閘門洶湧而來的時候,它會以一種當事人猝不及防的形式出現。
所以對大體系的迷信是一種人性的錯覺,而在大體系中生活久了,畏懼不確定性,則像高血壓、糖尿病、肥胖一樣是一種致命的富貴病。
去年國內火了一部網劇名叫《漫長的季節》,我不知您看了沒有,影片中一開場就表現了上世紀90年代國營大廠樺鋼的火車司機王響對自己一輩子生活的大體系「樺鋼」的迷之自信。明明廠子效益不好,各種危機接二連三的信號已經非常明確了,王響依然堅持「這麼大的廠子不會倒」「宇宙毀滅了,華鋼都會繼續存在」。

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我們當然可以認為王響看不清時代,但你不可否認,98年的那場下崗潮中,很多現實中工人真的就像劇中王響那麼想的。
他們就像鐵達尼號上的乘客一般,認為大體系已經「取消」掉了他們人生的不確定性,可是卻忽略了一個問題:一旦黑天鵝事件爆發,永恆存在的不確定性,會「加倍奉還」那些一心躲避它的人的麻痹大意。
所以我覺得,無論您做哪種決策,是留在國內還是陪愛人去美國,不要把「不確定性」當做考慮問題的關鍵,不確定性在哪個環境當中都有,只不過它們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歸根結底,以何種方式生活,才能把抵抗不確定性的能力抓在自己手裡,才應該是你做這種決定的關鍵。
提到抵抗不確定性、黑天鵝事件,我就想起了經濟學家、風險管理學說創立者塔勒布,他寫過「不確定性四部曲」——《隨機散步的傻瓜》、《黑天鵝》、《反脆弱》和《非對稱性風險》。
這四本書每一本都很有意思,尤其是第三部《反脆弱》,幾乎就是為了回答你的這種焦慮而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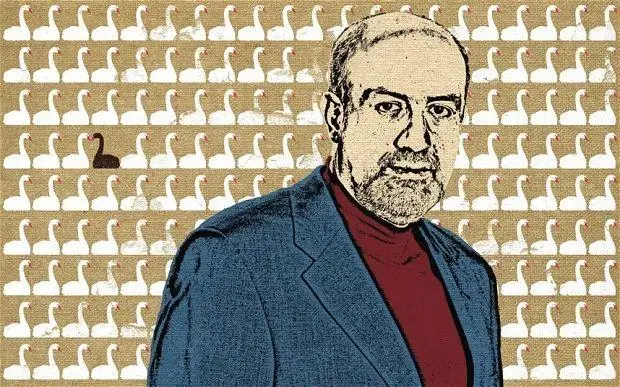
在《反脆弱》一書當中,塔勒布問了一個問題:一台大機器(比如一台洗衣機,甚至一架波音747客機)和一隻小動物(比如一隻小貓咪)相比,哪一個更脆弱呢?
很多人會想當然的說,那當然是小貓咪更脆弱了,大機械鋼筋鐵骨、龐大無比,小貓咪弱小無助、血肉之軀,這脆弱性怎麼能相比呢?
可是塔勒布的結論卻剛好相反,他說真正脆弱的反而是那些大機器,因為洗衣機和波音飛機都是機械體,它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自身沒有抗風險的能力,一旦機器上的某個零件壞掉了,又沒有人來修理,那整個機器就會癱瘓,甚至被摧毀。
相比之下,小貓咪雖然看似很柔弱,但它是生命體,生命體天然具有反脆弱的能力,你到健身房去擼鐵,那種鍛鍊的本質是拉斷你身體裡無數細小的肌纖維,可是這些肌纖維在損傷之後會進行代償性的重構更加粗壯的肌纖維組織。這就是生命體通過應激式的代償反脆弱的方法,或者用一句爛大街的話,生命的堅韌,就在於那些殺不死它的,最終會讓它更強大。
所以。不要幻想你能躲避掉不確定性,學會擁抱不確定性,並且把遭遇不確定性時抵抗它的主動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這才是「反脆弱」的關鍵。
具體到這位讀者來信談到的情況,我覺得她現在面臨的糾結本質上講,是她和她的愛人或者她的家庭和她的愛人,在反脆弱的能力上出現了分離:
她的愛人作為一個供職於跨國大公司的高精技術人才,如果選擇出國,他個人的反脆弱能力是會極度增強的,哪怕這家跨國大公司倒閉了,以他的技術和能力,以及相關產業在當地的興盛,應該也可以在當地另找一份不錯的工作,薪水甚至可能比原公司還要好,這就是塔勒布所說的代償性增強。
而與之相比,她自己或者說整個家庭的反脆弱力,在出國這個決定做出後,有可能確實減弱了,一雙兒女要在異國重新上學,她更要在異國他鄉過語言關、另尋一份工作。一旦遭遇不確定性,她們可能很難再重新開始,這就是塔勒布所說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創害超過了生命體所能承受的閾值,會讓生活狀態進入下行軌道。
所以我想,她的糾結,其實不在於該不該出國。而在於夫妻之間,或者說個人與家庭之間反脆弱力的此消彼長的矛盾,
所以,我對她的建議是兩點:
第一,你應該和你愛人好好談一談。重新評估、確認一下夫妻感情的堅韌度和雙方對家庭的忠誠度。看看這份感情是否也有足夠的「反脆弱力」,能夠經得起雙方出國後反脆弱力此消彼長這種變動的考驗。哪怕一方暫時做家庭主婦或家庭主夫,另一方能不能體諒並真的有能力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如果可以,出國是可以考慮的,因為這證明兩人的感情是一種生命體,遵循「殺不死我的,會讓我更強大」的準則,在異國他鄉,也許兩人的情感會在考驗中更加堅固。
第二,我建議你也應該重新衡量一下自己出國之後的「反脆弱」力。
情況未必真的有你想像的那麼糟糕。
我始終不太相信,一個人在有手有腳、有學習能力、且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的現代社會能養不起自己。
去年網上爆出過一對中國的「卡車夫婦」,本來在國內擺攤賣烤串勉強維生,後來走線去了美國,前期靠打工、後來靠自學開卡車過上了挺富裕的中產生活,買了房子,還把女兒接過去定居了。
再後來,這兩口子又發現了賺錢新賽道,靠發一些一邊在美國領救濟食品一邊嘲笑美國人傻的視頻在抖音上火了一把。
我看過這個視頻後,一方面覺得這兩口子靈魂里的貧窮確實無法治好,另一方面又覺得,在美國生活,可能真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難的一件事。你看這麼樣的倆貨都能在美國活下來,你即便不靠丈夫(或者妻子),難道真的不如他們麼?
當然聊到這一點,前不久《我妻之死》那位作者似乎是個反例,這哥們靠哭訴他自從離了他那能幹的妻子就在加拿大怎麼怎麼活不下去火了一把,拿了大筆打賞。
可是我總疑心這哥們是在賣慘騙募捐,要不然他天天這麼哭訴加拿大的水深火熱,可也沒見他回歸祖國懷抱啊?
如果你去了發現既沒有辦法自力更生、也不願意當家庭主婦或主夫,那你到時候再選擇回來也未嘗不是一個選擇。
總之,為什麼不先試試再說呢?
也許你的反脆弱力真沒你想像的那麼弱。
至於很多人可能會有一些更具體的情況,比如人在體制內或半體制內,一旦辭職出去了就不太好回來找這麼舒服的工作了等等……
我覺得還是最開始談到的那個問題,不要幻想你所棲身的大體系能夠幫你取消掉不確定性,它只是會讓不確定性最終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在你面前而已。
塔勒布很喜歡講一個「農場火雞」的寓言,他說一隻火雞從出生起每天都接受農場主的餵養,火雞一天比一天相信農場主是愛它的,它所生活的農場則簡直是一個規避風險的天堂,可是到了1001天,正當火雞打算表達這種感恩的時候,那一天剛好是感恩節,農場主把火雞宰了,當成了當天的晚宴。
這個故事經過大劉老師在《三體》中的普及,在國內知道的人也不少。
不過大劉老師在講這個故事時——如同他講很多其他西方故事時一樣——把這故事的原有意思給扭曲了。
塔勒布講這故事的本意,是人要做「生命體」而非「機械體」,要主動擁抱不確定性風險、要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要擁有反脆弱的能力。
像農場火雞一樣生活在永恆的舒適區,把農場外的不確定性看過一種必須規避的風險,這樣的生活看似安逸,其實具有更大的風險。而且尤其可怖的是,這種風險將何時以何種方式到來,你自己無從主宰、甚至無從得知。

那位讀者,以上就是我給您的問題的回覆。
非常抱歉,雖然寫了4000字,但還是沒給您一個明確的答覆。最後,只以這樣一段話送給您吧:
我總覺得,正如不經歷辛勞就不懂得財富的甘甜,不經歷考驗就難言信仰的堅固。一種不敢於或者直接被掠奪了不確定性風險的人生,是不值得一過的。這並不僅僅因為不確定性終究無法別取消,只是最終會換一種方式被折算。更因為,生命本身,本就應當是一曲關於自由與追尋它的勇氣的讚歌。
你此生的答案,終將從你怎樣擁抱不確定性中獲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