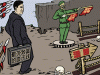壁畫《潑水節》局部
1980年代,北京工藝美術學校的4名畢業生,相約去首都國際機場看一幅裸體壁畫。他們中有個同學的姐夫老耿,在首都機場工作,他說,在他們餐廳有幅裸體壁畫,很多人排著隊看那個。
四個人中的門欣熙說,不大可能。因為那個時候,別說裸體,像他們上課畫的模特,都穿著泳裝,說是做人體,實際都穿著泳裝做。怎麼可能?
但老耿一再強調是真的。於是門欣熙也就不再堅持,與同學一起前往機場看個究竟。
到了機場一看,發現那個壁畫是拿布擋著的。隔著擋布希麼也看不見,只有掀開才能看到。一開始誰也不敢去掀,後來看見有人掀了,探頭進去欣賞,四個人才大著膽子過去掀那擋布。掀之前大家約定,如果有人上來干預,就拿畢業證亮給他看,表明自己是美術學校的學生,憑學生證可以去展覽館美術館看展覽。總之,別讓人家把我們當流氓抓起來了。
這幅被遮擋的壁畫名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在高三米四、長二十七米的牆上,描繪了傣族人過潑水節的情景。壁畫由兩大部分組成,在正面的牆上,展現的是傣家人擔水、潑水及舞蹈的場面;在東側那塊面積較小的牆壁上,描繪的是沐浴和談情說愛的場景。正是沐浴這部分的內容,出現了裸體,在壁畫展出幾個月後,被遮上了一塊布簾。
壁畫的作者叫袁運生,此前極少有人知道,就因為他畫的兩個傣族少女,突然間名噪一時。
1955年,袁運生以第一名的專業成績考入中央美院。當時的教育環境,在藝術觀念上一邊倒地學習蘇聯。但袁運生受指導老師董希文的影響,選擇將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主義造型語言相結合,作為自己創作的方向。
1962年畢業前夕,袁運生在江南寫生兩個多月的基礎上,創作了油畫《水鄉的記憶》作為他的畢業作品。畫面以蘇州郊區的甪(lù)直古鎮為背景,採用中西藝術交融的形式,描繪出了他對江南古鎮的理解。
老師董希文對這幅作品非常滿意,給出了5分的滿分,而主張全面學習蘇聯造型語言的李天祥老師卻給出了2分的評級。兩位老師為此爭執不下,最終達成妥協,給了個4+。
不久,批判這幅畢業作品的文章刊登在了雜誌上,理由非常荒唐,說這張畫「醜化了勞動人民的形象,把他們畫成體態畸形和有暗淡情緒的樣子」。
因為這個緣故,畢業時,儘管美術大師龐薰琴先生親自來中央美院,指名要袁運生去中央工藝美院任教,但袁運生最終還是被分配到了長春市工人文化宮,做了一群業餘繪畫愛好者的輔導老師。
1978年4月,中央下達了摘掉右派帽子的指示,袁運生和全國的右派分子一道,紛紛去除了附著於身上的特殊標籤。卸下了精神包袱的袁運生,心情舒暢地去了雲南。年底,正在雲南寫生的袁運生,突然接到中央工藝美院院長張仃的邀請,要他前往北京,為新落成的首都國際機場創作壁畫。
袁運生受到邀請後的第一反應,立刻就想到了潑水節。他要在分配給他的一面寛27米、高3.4米的巨大牆壁上,畫一幅傣族風情的壁畫。他根據牆壁的實際情況,決定在側面牆上描畫沐浴和愛情的主題,以兩個傣族姑娘健康、苗條的身軀,表達對人體的讚美。
但在當時,要畫裸體還是很犯嘀咕的。
費正和袁運生同是中央美院62屆畢業生,他們上學期間還上過人體寫生課。但在他們畢業不久,人體課就在中國逐漸銷聲匿跡了。
1978年考上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的陳丹青,還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上人體寫生課的情景。「我們九個人裡面只有兩個人對這件事情不是那麼驚訝,因為他們在文革前畫過人體,……我們九個人裡面只有兩個沒有結婚……單身意味著你還沒有看過裸體……你直接看到一個異性的身體,會是怎樣一種感覺?社會上也把這種事看得非常神秘,說這個院子裡的人在畫裸體。」
當時有個叫錢紹武的雕刻家,很勇敢地做了一個關於裸體藝術、裸體美的學術報告,放了兩張圖片,來聽報告的人擠滿了禮堂。當光線黑下來以後,像維納斯這些裸體雕塑,以及其他一些油畫,一放出來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很莊嚴地都在那裡看著。幾百號人,窗戶上也趴著人,外校趁黑湧進來一些人,聚在那裡,就想看裸體。
處於當時那樣的社會環境,袁運生的壁畫創作,自然免不了會經歷很多曲折,才能夠最終出現在機場的牆壁上。
為了不受干擾,袁運生選在一天下午,大家都開會去了,他利用這個機會,把幾個人體都一併畫了。畫了就成了既成事實。有個主管宣傳的官員,走來看了以後,心裡有點打鼓,他說這個事情要等小平同志看了以後再做決定。
鄧小平答應可以順便過來看看。1979年10月的一天,鄧小平到首都機場參觀,當時好多人陪著,袁運生和費正事前並不知道,有人介紹說這就是壁畫的作者。不少人說這個人體好像不應該有,為此產生了爭論。想聽聽領導的看法。鄧小平站在壁畫前,沉默了一下說:「這有什麼好爭議的,藝術表現很正常。我看可以。」
最初,整個機場壁畫贏得了贊聲一片。新華社工業部記者李安定在報導機場建設的同時,專門寫了一篇評論壁畫《潑水節》的文章。文章寫到:這幅表現傣族人民熱愛生活,追求幸福的作品令人賞心悅目,尤其畫中的沐浴部分,兩個姑娘健康、潔白的身軀,更加凸顯了傣族人民的純潔和質樸。
就在這一片讚賞聲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此時42歲的袁運生正為調入中央美院做準備,突然被告知要在他的壁畫前召開一場現場討論會。討論的內容特別令人無言以對,說是壁畫中沒有拖拉機也沒有高壓線,人還赤腳,傣族同胞是有塑料鞋的,怎麼不穿?反而裸體這個話題沒有怎麼說,說的都是思想政策性的。
好在調動沒有受到影響,袁運生在1980年6月正式調入了中央美院,在美院不長的教書期間,他風聞自己的壁畫要被毀掉。
那段時間,《美術》雜誌正在發起一場「關於正確對待人體美術」的大討論,這一期雜誌刊登了大量國外人體圖片。
在隨後一期的雜誌上,刊登了來自各地的讀者來信。其中昆明讀者黃振瓏在來信中說:「我知道海關查私,也把裸體圖片作為一個目標去搜索。貴刊承認社會主義文藝同資本主義文藝有區別嗎?難道欣賞屁股、乳房就是貴刊的現代化嗎?」
陳丹青後來評論此事說:老百姓看待這種事,可能比知識分子更開通;其實那些故意鬧騰的,都是有點所謂文化的人。
因為閒話多了,還為此專門召開了座談會。會上,藝術家們各抒己見,就連在中央民族大學學習的傣族學生也被請來參加座談,聽取他們對壁畫的觀後感。有人建議袁運生修改作品,給裸體人物穿上衣服。對此,袁運生拒絕修改。
在紛紛擾擾的聲音中,首都機場曾一度在壁畫前拉起了幕布。但專程前來一睹此畫風采的民眾,還是絡繹不絕。
這場圍繞壁畫展開的討論,一直持續到80年底,才驟雨初歇,漸入尾聲,結束時還有人憂慮一問:「人體美術在中國民族中能紮下根嗎?」
這一年,爭議從美術界擴大到了音樂範圍。一首《軍港之夜》,因為歌詞「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也遭到非議,爭議的問題是,士兵們都睡覺了,誰來站崗?
此時,在中央美院新成立的壁畫系擔任教學的袁運生,已經無緣壁畫創作。
1982年,袁運生前往美國求學。他走後不久,壁畫《潑水節》中的裸體部分,因為用布簾遮攔仍然擋不住有人掀開來看,索性再釘上三合板徹底封死。
8年後,袁運生第一次回國,遮擋在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前的三合板已經拆除,再次以美麗無暇的身姿,坦坦蕩蕩地面對遊客的欣賞。
時間改變了觀念。回頭再看那場爭議,恍若隔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又過了8年,首都機場第二次擴建,規模更大的二號航廈取代了老航廈。
2004年,裝修過的老航廈重新啟用,當年轟動全國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被安排做了三樓一家餐廳的背景。
與人來人往的新候機大樓相比,經過這裡的墮胎量明顯少了許多。在這裡就餐候機的旅客,幾乎沒有人關注那幅大型的壁畫。
但新的爭議點仍在不斷冒出,比如俄烏戰爭,比如以哈衝突。這個世界仿佛總是處於紛擾之中。
2024-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