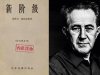陳夢家、趙蘿蕤夫婦,1936年。
1、書
在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圖書館,一本書的書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我來到安陽這個河南小城是為了研究當地的文物古蹟。根據歷史記載,該地區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榮興盛六百多年後,於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滅。據記載,商朝的滅亡禍起荒淫——傳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後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裝美酒的大酒鬼。不過,這本書是我發現跟美國人扯上關係的第一條線索,讓我不禁細看起來。
沒有作者名。該書出版於1962年,印著八百多張商、周銅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國古代冶金術最發達的時期之一)。每一件銅器,書里都提供了帝國主義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錄里有多麗絲·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銅器)、艾弗里·C·布倫達治(三十件)和阿爾弗雷德·F·皮爾斯白瑞(五十八件)。
圖書館裡有一位年輕的考古工作者,我問他知不知道那本書是誰寫的。「陳夢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專業就是甲骨文。他還是個著名的詩人。」
甲骨上雕刻著東亞地區已知最早的文字符號。甲骨原料來自牛的肩胛骨和龜的胸甲,常用於商朝宮廷的占卜儀式。我問那位考古工作者,陳夢家是否還在中國。
「他死了,」年輕人回答道。「『文革『期間自殺了。」
我合上書,問安陽考古站還有沒有人認識陳夢家。
「去找老楊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陳夢家在北京自殺的時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對面就可以找到老楊。」
在安陽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並不多,工作站有十來棟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數房子用來存放文物。微風吹拂著梧桐樹,遠處間或有火車轟鳴而過,這裡離北京只有六個小時的火車車程。除此之外,周圍一片寂靜。四周修著高大的圍牆,圍牆上架著倒刺鐵絲網。
我在一間布滿灰塵的會議室見到了老楊——楊錫章。他六十六歲,鑲著滿口銀牙;他每次微笑,總讓我吃一驚,有如瞥見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閃爍發光。老楊告訴我,陳夢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銅器的。陳當時身在美國,同在美國的還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的妻子趙蘿蕤。趙蘿蕤出身於深受西方影響的中國家庭,她的父親是聖公會牧師,也是北京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院長。
「所以陳夢家麻煩不斷,」老楊說道。「他老婆家跟外國的聯繫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夢家就被打成『走資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還是男女生活作風問題。」
這個詞彙我很陌生,於是便問其詳。老楊表情頗不自然地笑了笑——銀光一閃。「意思是,」他過了一會兒才回答道。「你跟一個不是你老婆的女人發生了關係。」
「陳夢家做過這種事?」
「不太清楚,」老楊回答道。我身後是一面窗戶,他無言地凝視著窗外。我問起陳夢家的自殺,老楊繼續說道:「這事兒發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陳夢家第一次自殺的時候,大家把他救了下來。之後,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幾個年輕人去看著他。但我們不可能二十四小時和他待在一起。」
老楊指了指窗戶,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斑駁的陽光灑在外面的樹蔭下。「想像你就在陳夢家北京的家裡,外面是一個院子,」老楊說道。「一天,陳夢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閃而過。」老楊做了個一閃而過的手勢,仿佛跟著一個想像中的人,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之外。「過了幾分鐘,我們才發覺他跑了。我們追出門,可還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楊說,陳夢家的妻子沒有住在那裡,因為紅衛兵正押著她在北京大學遊街。我問關於美帝國主義者的那本書為什麼沒有署陳夢家的名字。
「1957年,陳夢家批評過領導的一些觀點,」老楊說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書。可那本書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楊在辦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鑑,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頁。照片裡的陳夢家還是個中年人,他長著酒窩,眼睛明亮,一頭黑髮油光閃亮,穿了一件舊式的高領襯衫。在所有人中間,他的笑容最為燦爛。
幾個月後,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歲的學者,他給我講了這個故事的很多細節。1950年代,毛澤東提出用字母替代漢字書寫,陳夢家持反對態度。捍衛漢字是他的第一項主要政治錯誤。
2、骨
在人類文明史上,漢字顯得十分獨特:這一套書寫系統的基本結構原則自商朝以來未曾改變過。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漢字由象形符號(一個字代表一種事物或意義)演化成表意表音符號(一個字代表一個讀音)。公元前2000年,近東地區的閃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轉化成人類的第一套字母體系。字母書寫系統比表意表音符號更具靈活性,因為字母可以把一個音節細分為更小的單位。這使拼寫系統用於不同的語言乃至方言變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語書寫者可以此區分讀音正規的「what」與帶有倫敦腔的「wot」。
漢字是唯一未被棄用或被轉換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號,結果導致人們所讀和所寫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差異。就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期而言,正式書寫採用的是古漢字,這種文字符號在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發展並僅存於書面語言。到了20世紀初葉,改革者們成功地使正式書寫系統遵從一種被稱為普通話的北方方言。
漢語口語並不是一種單一語言——語言學家有時把它的多樣性比作羅曼語族。一位語言學家告訴我,北京人所說的方言和廣州人所說的方言實際上有如英語和德語。如果中國採用字母符號,寫出來的文字就能反映這種差異,但在表意表音符號體系下,很多口頭語言無法加以書寫。例如,東南沿海浙江省的某個人如果要識文斷字,首先得學會普通話。大多數南方人所書寫的文字實際上是一種第二語言。
這套書寫符號從技術上說具有一定的難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個人需要識記四千個漢字。儘管這些漢字原本包含的發音和視覺線索十分清晰,但許多線索由於發音改變而被逐漸淘汰,這使得漢字更難識記。儘管如此複雜,中國人並不缺乏學習的雄心。
中國文化多與書寫有關——書法作品是最具價值的藝術形式,繪畫作品通常要有顯眼的書法題字。人們在某些時候會支起專門的鼎爐,很敬重地用於焚化寫滿文字的一摞摞紙片。到17世紀,中國已經建立起完善的商業出版體系,讀寫能力比起歐洲的很多國家來能涵蓋更廣大的社會階層。匹茲堡大學的歷史學家羅友枝(Evelyn S. Rawski)估計,18、19世紀中國男性的識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間——相當於日本和英國工業革命前的水平。
這一套書寫系統也有其他優點,比如它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非凡能力。一個具有讀寫能力的中國人無論來自何方,他總能讀懂另一個中國人寫出來的東西。而且在面臨古時候留下來的文字作品時他不會覺得遙不可及。當甲骨文在19世紀末被重新發現的時候,中國的學者們幾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識——完全不同於埃及的象形文字,羅塞塔石碑被發掘前的數百年間,無人能識別這種文字。
兩年前,我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煒(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類似專家全世界可能不超過三十人。)吉德煒告訴我,他一直痴迷於漢字和中國先祖崇拜之間的關聯,後者正是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