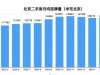可憐那些學子與平民,竟不曉得他們從一開始就觸犯了天條,而去幻想他們響遏行雲的呼號和森林一般揮舞的手臂能正天聽、挽狂瀾。
這個政權是暴力革命的產物,最終也要用暴力來捍衛它。想變天嗎?無妨一試,但他們當年流了那麼多血,你們就要還這麼多血來。這絕不是戲言,而是見諸《人民日報》的大塊文章和政要的公開講話。這叫打開天窗說亮話。什麼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類都被簡化為――到底是你還是我來坐江山!
這正是現代中國的困局。執政者已斷然排除了和平變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蒼生之福,又會墮入強權陰謀和政治仇恨的歷史因循之中。說到底,千年來每一次改朝換代,終不離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說這是一次創世紀的偉大嘗試,其結局竟也並無例外。
九、
我離開了煞氣重重的崇文門,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後景像,又發現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瀝青層大面積龜裂損毀,當為重型戰車轟隆輾壓所致。就在某個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絕跡多時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這些細節,或許有助窺探屠城黑日之軍與警的微妙關係――
路心的交通崗亭已被戰車撞翻,交通警背著手站在路邊,無所事事。馬路已無正常交通,民用車輛極為罕見,卻不時有拉著「為民送糧」橫幅的軍車在未及清理的障礙物之間繞行。顯見得在居民的搶購風之下,首都存糧已見危機。再者,廿萬入城大軍的給養消耗也頗驚人。交通警神情沮喪地目送著軍車,那些車牌標誌和識別號碼是他聞所未聞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應以滿口京腔,於是一下子圍攏了好些平民問這問那,我正好聽到兩句對答。市民不知問的什麼,警察嘴角向遠去的軍車一撇:「他們連我們也打!」市民又問:「這些大兵在北京還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問我,我問誰去呀!」
可以想見,戒嚴部隊的總攻時刻、行動路線以及「強制措施」的具體所指,首都交警大隊全都蒙在鼓裡。我記得第一支從西南路衝擊廣場的軍隊前鋒殺至,在靠近前門的「東方明珠大酒樓」路口值勤的交通警還在崗上,當其時那位警察也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戰鬥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論,凡長駐北京的衛戍區官兵、武裝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戶籍警察甚至包括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內心大都同情民運,只不過交通警察僅系準軍事組織,與公務員近同,政治紀律不那麼嚴密,故能斗膽講幾句大實話。
甚至於軍隊,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經過某重要路段,這裡有多輛軍車殘骸,其中一部履帶式軍車燒毀得那樣徹底,以我對兵器的無知,竟認不出它原先是裝甲車還是一種軍事指揮車,總之燒成一堆廢鐵,右邊一大截履帶脫落,像一條僵死的巨蟒癱在路心。一切都顯示當時戰況之慘烈。此處現駐紮著大隊士兵。我初時驟見路邊綠地竟然坐滿了穿草綠軍服的大兵,嚇得幾乎掉頭而去,卻又恐顯得形跡可疑,唯有硬著頭皮向前騎行。殊想不到這裡的氣氛要比前門、崇文門輕鬆百倍。兵們摘下鋼盔,敞著風紀扣,在草地上矮樹下或坐或臥,像郊遊野餐似的。只有當官的仍戎裝肅整,挎著手槍四處遊動。他們對路心的劫後景像熟視無睹,事不關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層住宅樓群。那些不識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悶多日,擇這好天氣下樓撒歡來了。士兵們很喜歡逗孩子玩,百無禁忌的小童鑽入士兵叢中,連跑帶跳。兵們樂不可支,或摟抱,或將孩子舉放於軍車上。孩子們的父母先是戒備而後也趨前拉話。我見狀也下車緩行,聽見許多對答。市民的問話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們是瀋陽軍區開來的,六月五日才進城,一直停留在這裡。有的兵為了回應尖銳質詢,拉開槍膛給市民展示裡頭並無子彈,又說他們這一路根本沒有配發彈藥;有的兵被問道,路心被毀的軍車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當官的根本無意監聽部下的對答,至於市民更大膽的話語,當官的都裝聽不見。
可惜我無法多作逗留,目標是安定門――首都機場――廣州。每一階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謹慎從事,少去招惹,以免無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線圖,我繞開重兵把守躲、殺氣騰騰的建國門立體交叉橋,也避開大片使館區,但散布好幾處的外交公寓總不能完全繞過,也就看到了一些戲劇性畫面。這裡多了些小轎車,均系外交官的黑色專用牌照。這些轎車都裝扮得像慶典花車,除了車頭兩面國旗招展,車後天線杆也綁上更大幅的國旗,車身則貼滿五顏六色的外國國徽,隔一兩條街也識別得出這是外國使館的專車。我想,這是派駐那些政變頻仍、內戰不息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習慣沿用的應變措施,卻在北京派上用場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僑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裝運大小行李,連等候上車的外國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國旗。
即使未曾親睹六四慘況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場景,便可相信這個國家的確發生了一場戰爭――一場專制對民主、野蠻對理性的戰爭。
十、
終於到達安定門約定地點。劉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車裡沒動,只用失神的目光打個招呼。
我認得《人民文學》的車,司機卻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給王蒙開車的老楊司機,也不是那位曾給「借」出去拍過兩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國武術冠軍。
我把單車放到地鐵站出口處。相信妻子要過好多天以後才敢到這邊來取――如果它還在的話。
鑽進車裡,劉心武簡短說幾句有關機票和航班的事,便歸於沉默。司機亦無言。這張生面孔令我頗不安,更不敢多話。再等一會。《人民文學》的王清風來了,我稍覺寬心,是他送我們去機場。
車子發動,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異的戰亂景像,四人都各懷心事,默不作聲。直駛離城區,開上通往首都機場的公路,王清風才給我介紹,這位年輕司機也是剛「借」來的。大陸單位的司機時常被借來借去,不足為怪。介紹畢,王清風也不再多言。劉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機場的道路並無軍隊蹤跡,更無截查哨卡,這倒是怪事。內亂一起,占領電視台、電台、電訊電話局、報社、機場都是通例,亦系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範例和光榮傳統…..機場指揮塔從平坦的柏油路盡頭迅速崛起,第二個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際稍稍鬆弛的心弦又再抽緊,包括司機在內,一車人都頗覺不安,實不知此刻首都機場成了什麼樣子。
拐入停車場,又看到多輛撤僑巴士。前些天儘管各國馳電緊急撤出僑民、專家、留學生,卻無法抵達機場,有先見之明的英美等國,在五月份戒嚴令生效時已包租下靠近機場的假日酒店,臨時安置僑民,一有風吹草動便直奔國際機場。那些動作稍慢的則要滯留到這時才得以返國。
望去國際航線候機廳門口淨是箱籠行李、男女老幼;國內航線大廳之混亂更難以想像。然而,我們之憂慮倒不在於此,機場如無戒嚴部隊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統的人馬把關,重點甄別和防範「XX分子」出走。我們都不清楚自己是什麼「分子」,總之,所謂空弦落雁,鐵腕強權之下「知識分子」永遠是驚弓之鳥。
王清風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強幹。他讓我們安坐勿動,證件交他去辦理登機手續。王才進去一會就轉回,一切辦妥。他說國內航線反而很冷清,多數國內搭客都困身城內,無法前來。聽機場工作人員說,昨天飛廣州的航班才六個乘客。看情形,大廳里也並無異常情況。
我們其實到得太早,這種時局勢必要加大時間提前量。接下來,只剩下沉悶的等待。我自是無話可說,只聽見劉向王交待若干編務,其中提到已徵集多時的《人民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其實,在紀念冊上賦詩題詞的群賢,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運已難預料……
十一、
終於起行。我和劉步入大廳,果然不見了太平時的熙熙攘攘,但旅客還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內氣氛已略見鬆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線辦理機票登記之處,都是清一色民航職員,並無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進而又留意到,一些樣子太過年輕、神情卻憔悴不堪的乘客,他們是臨時前來購票的。機場的慣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內民航售票處預購,只有個別常年出差而又門檻很精的人才曉得如果某班航機有空位,機場間或也發售即時機票,但仍須出示個人證件以外的單位證明。而我看到現時這些臨時購票者似無此類單位證明,口頭向民航職員詢問交涉,然後一亮窩在手心的證件――我相信那是學生證,機場職員一改平素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麵孔,慨然允諾,並即刻著手辦理,收款、開票――就這麼簡單快捷。
這些細節,我想劉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們沒有交流感想,只低頭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現的武警制服,是進入候機休息廳的檢查關卡,此處向來就有的,一切運轉依舊,也許只是我的心理感覺,那幾位男女武警對學生模樣的乘客的檢查放行,似乎比旁人還快捷利索(後來我得知,機場很快就被嚴密控制,此前的鬆緩再不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