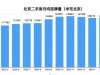一輸到底,再無翻本的機會了。
列成方陣的巨型坦克群之間遊走著閒散計程車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滿行軍被,潮滋滋的草綠色被褥在盛陽之下暴曬,坦克手三三兩兩坐在炮塔上,饒有興致地眺望著天安門廣場四周氣勢雄渾的建築群。這裡城廓連雲,大道朝天,和他們那溝壑縱橫、沙塵滾滾的訓練基地是多麼不一樣啊。這群鋼鐵雄獅在宏偉帝都的中軸線上振鬃嘶吼,重重疊疊的皇城宮闕亦為之抖索,那種征服感是何等豪邁!
五十年代初,他們長驅直入南韓的漢城。
六十年代初,他們擊潰麥克馬洪線南北的印度軍隊。
七十年代末,他們一舉攻陷越南的諒山。
八十年代末,他們以雷霆萬鈞之勢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滯的路人踏上這條中軸線,都喪魂落魄地向廣場行注目禮。這就是剛剛向全世界獻演過一出英雄史詩的地方嗎?這就是一個共和國搏動的心臟嗎?
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兩回從無盡的庸碌灰暗裡噴湧出熾熱奪目的崇高感、壯烈感,並真切體味到「國家主人」的瞬間感覺,那正是在這裡――天安門廣場。
它是人民的圖騰。它是歷史的祭壇。
它其實從建成之日起就忠實於這兩種功能,如同廣場鋪設的方磚一樣精確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縝密地計算過,它既能支撐起學生的連營帳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輾壓?
我移目向蒼天,正陽門彩繪描金的飛檐傲然翹向陽光,上面浮凸的飄逸行龍仿佛不曾被硝煙燻過,只有驚恐的燕群像黑色箭杆一樣在箭樓上飛出飛入。放眼望,皇城隱隱,宮闕重疊,天安門、端門、午門……都在赤日下裸呈著血樣的顏色。數千年來,帝國天朝都認定這種色澤是皇權與威嚴的像征,午門之外,多少顆貯藏著異端的頭顱在刀斧手腳下咕嘟嘟滾動,狂噴出來的鮮血只能讓史家的春秋之筆變得更加生動。這個帝國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來就充滿了血腥味。
然而,這一代從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搖籃里長大的中國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這反差巨大的變化。他們呆立於哨兵的視界和子彈的射程之內,眺望人事皆非的廣場,儘可能抹去臉上的表情,但還是有許多人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我站立了十分鐘,此際的感覺卻比六月三日至四日無眠的晝夜還要漫長。我覺得自己正在與一個時代訣別。
這個時代只有十年,在時間之河裡它是那麼倏忽短暫,而就這輩人而言卻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這個時代的變遷在人類進步史上本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而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度來論卻又是非凡的、充滿想像力的;它從千年魔瓶里剛剛釋放出一個民族的精魂,轉眼又被加蓋密封,埋葬在刻滿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
而這個時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門廣場。同樣在苦寒的春天,這裡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萬哀兵的和平大起義,結局是鮮血濺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漢白玉基座。
廣場總是在製造著英雄和烈士。一個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運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無端念及一則軼事――殘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人民初嘗久亂之後的安寧,有一位著名的城建專家在《光明日報》撰文提議:如今不再是「階級鬥爭」年代,不再有英明領袖檢閱百萬「革命群眾」的場面,廣場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鑑於這一片城區綠地偏少,不如將廣場翻種綠樹,變為一個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園。不消說,這種腐儒式的專家論調,既不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首肯,亦決不可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
今日驀然回首,那位學者的立論豈非確有先見之明?又經這一遭創巨痛深的歷史事變,廣場的綠化夢更無從談起。歲月悠悠,統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廣場視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聖地。它是永恆的。
廣場,這是你的宿命。
我離開了它。我如果曉得此去就不再回頭,心底感觸更將如何?十年來,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開闊圖景,而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於我頭顱內凹凸不平的腦質層里。
八、
前門東大街。過了北京市警局,我開始騎行,單車像載不動那紛紜意緒而哐啷作響。長街兩側緊閉的店鋪次第退後……途經兩家銀行,更是鐵閘把門,似乎有不少人是奔著它出門的,到銀行門口焦躁地張望一陣,又掉頭返回。擠提存款,乃亂世必然伴生之事。儘管沿街了無生氣,但我的直觀印像是――六四當日並無大部隊從前門東大街殺過來。我選擇這條路線而避開長安東大街,顯然是明智的。但這一來,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經崇文門,這個向來令人頭疼的交通瓶頸,如今意味著惡戰、暴戾和軍民之間的深仇大恨。
儘管我從電話里聽到不下三四種版本的轉述,當崇文門呈現眼前,我才曉得自己的想像力是那樣貧乏――這裡不比廣場、前門,崇文門的路障雖是草草清理過了,卻只是勉強打通了道路。那些燒得焦黑、呲著扭曲框架和鐵殼的大小車輛被推到路旁,還有一輛傾覆的甬道式大型無軌電車無法拖動,堵塞著半條馬路。滿地是碎磚和閃閃發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淨的黃澄澄彈殼……這裡的步哨不及前門多,氣焰卻兇橫暴戾,食指鎖定在槍扳機上,盔沿下雙目精芒閃動,掃描著每一個路人,不時發出幾聲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驚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橋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著刺刀的崗哨,不再有市民過往。當日在此慘酷的一戰,成了官方指證「反革命暴亂」最有力的說辭。
我無意細述事件的過程,所謂「歷史事實」,在它剛發生不久,就已各執一詞,真偽莫辨;及至時過境遷,就更說不清楚了。我倒願意引述官方控詞的梗概――當日,大隊軍車滿載全副武裝計程車兵由南嚮往北,朝廣場方向猛撲,突進至崇文門這交通瓶頸,已是路障重重,民眾嚴陣以待,磚石與瓶子劈頭蓋臉飛來。指揮官眼見無法前進,下令所有軍車掉頭另覓通途,僅一輛拖卡的軍車因體積笨重而掉不過頭來,轉眼後繼部隊已移師他往,撇下這一小隊官兵受到民眾的包圍進逼,他們棄車之後被困於行人天橋上,由士兵持槍把守兩邊梯口。民眾吶喊不止,卻不敢硬沖;其後,有三位白髮老婦挺身而出,顫巍巍地走上面天橋,跪倒在士兵腳下,哭泣懇求當兵的勿以槍口對準學生和百姓――到此為止,本是八九民運中感天動地的一幕――那士兵猶豫不決,這時有人發喊:這當兵的手裡欠下幾條人命!無論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極具刺激性,於是有幾條身形暴起,和當兵的扭打成一團。指揮官見勢急令全隊衝下天橋,奪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這名士兵已無法走脫,先被打暈,又被扔下天橋,最後被倒吊於橋底,給澆上汽油,點了天燈!
這毛骨悚然而又極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報全軍,其後又印發照片、登報紙、上電視,成了激發戒嚴部隊士氣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聽到的並不是這個官方說法,但無論何種版本,我都為之深感震駭。這民族的潛意識中的嗜血和暴力傾向竟是如此可怕,爭端一起即血濺五步,慣於用生死來判勝敗,用斧鉞來辨正邪。如此國民性,欲向現代文明和理性歸化,真是荊棘滿途。
我曾大覺困惑,這個國族的傳統形像倒是沉靜內斂、十分儒雅的,那些綿永而湮邈的歷史,在外人看來,簡直是個瑰麗的東方神話。至少,構成中華文化主流的儒釋道三家,均無暴力取向,如果說「國民教育」儒家學說有相當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統、貶抑異端,確無鼓吹暴力的教條。思前想後,只能歸咎於手執王杖的權勢者,那些君臨一切的真龍天子,那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諸如「點天燈」這種狂暴的殺人術,本來就是王者首創,車裂、鼎烹、宮刑、瓮焙、綁縛法場的遊街示眾、刀斧手在觀者如堵之下誇張的表演、割下首級高懸城門昭告子民……所有這些野蠻暴行都假王道、綱常、社稷、穩定之名公然施行,從而激發和確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衝動成了草澤民間的潛在規則。事實上,新中國建政數十年來,一直沿襲許多先朝的律例,諸如處決「階級敵人」的群眾公審大會,押赴刑場時的掛牌遊街,更不用說推陳出新的鬥爭會,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發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為那名士兵的悲慘下場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緒藉以宣洩的一個不幸對像。
但是,這些「暴民」難道是從地底陰溝鑽出來的嗎?在這個血腥的六月之前,他們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還是如官方所說,是一些對社會主義制度懷有深仇大恨的敵對分子?
如果歷史需要證詞,我會毫不猶豫地以親歷者的身份,證實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擊的好幾個重要現場,絕無所謂「反革命暴亂」的半點跡像。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門,也難以讓我相信整個進軍過程中一彈未發,簡直就像開赴天安門廣場參加閱兵式似的。這一點,崇文門一帶的市民當然有不同說法,否則無法置信一兩個煽動者能令群情聳動,霎時釋放出以暴易暴的潛意識。然而,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則性問題,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鎮壓,「一步也不能退」,「斬草除根,除惡務盡」這就是他們的鐵腕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