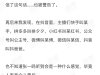四
書中還有四個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應該都是有現實原型的,具體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氣質十分邊緣的人們,如何逐步進入了「歷史」的大門。在一個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體的個案。其中《阿爾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個。這個人本身追求完美、純潔,力求無懈可擊,這使得他的選擇帶上了一層悲劇色彩。
這是一位作家,在戰爭期間也會以作家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他創辦了地下文學刊物,寫作有關「受難」、「忠誠」主題的小說,表達了與納粹決一死戰的抵抗戰士的精神狀態,對於小說中的主人公來說,祖國和榮譽高於一切。然而,還存在著個人信念之外、比個人信念更為強大的力量。那就是「現實」。實際情況是,地下抵抗帶來了重大犧牲,同時更多的人在集中營里被槍決。涉及到成千上萬人的命運時,僅僅個人擁有的「忠誠」概念便顯得遠遠不夠。
1944年的華沙起義,將這個問題推至極端。這是由遠在倫敦的波蘭「地下國家」發動的。其時蘇聯軍隊已經到了易北河對岸,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紅軍的馬匹在河邊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複雜性在於,波蘭人對於俄國人同樣憂心忡忡,深知其吞併或或瓜分波蘭的野心不死。因此,對於指導起義的流亡政府來說,便期盼能在紅軍到來之前,有一個已經運轉的波蘭政府,這樣才有可能將主動權掌握在波蘭人自己手裡。這個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現實卻不允許。
米沃什形容為「這是一隻蒼蠅反抗兩個巨人的搏鬥」,其中一個巨人(俄)比另一個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著蒼蠅被一個巨人殺死之後它才出場,始終按兵不動。結果是,兩個月內華沙上空濃煙滾滾,手中武器為手槍、手榴彈、燃燒瓶的人們,完全不能抵擋來自德軍的轟炸機、坦克和重炮,二十萬人痛苦地死於殘酷的巷戰,華沙變成一片廢墟。倖存者逃進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誠於他的波蘭祖國,而不是屈服於蘇聯紅軍,會被當作「起義的法西斯」。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死路,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忠誠」,便顯得無效、愚忠、狂熱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憶了他本人與這位道德小說家,一道迷失在華沙起義後的廢墟瓦礫中的情景,他們「發現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幻想中的月球景觀。這裡一片沉寂。」一個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現了。它吊在一個金屬柵欄上,上面用紅色的漆寫道:「茲比舍克中尉的受難之路」。誰是這位茲比舍克中尉?有誰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樣的折磨?他所攜帶的是什麼樣任務?他是誰的兒子?或許是一個郵政官員的兒子?沒有人知道這些了。那塊木板上的字,就像是「從一個被毀棄的大地拋向天空的一聲吶喊」。一對朋友同樣承受了這個來自死亡邊緣孤獨聲音的巨大衝擊。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們,便懷著這樣無邊的絕望。而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經的思想道路:「他們能做什麼?逃到森林裡去?上吊?可是他們想活著,並且樂於接受重建國家的口號,最後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樣說話時,他幾乎是是帶著疼痛喊出來的。
那麼米沃什從什麼地方開始走向「歧路」?他與朋友的分歧出現在何處呢?他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通過他的敘述完全可以找到線索。這位被他化名為阿爾法的朋友擁有一種天生的抽象性,對於概念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具體人們的興趣,他的小說中具體的人們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變成衣從概念的需要。此類需要也是建立權威的需要。而對於米沃什來說,具體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們,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爾法寫出了他的新小說,關於納粹期間的華沙生活。米沃什這樣評論道:「阿爾法在被蹂躪的城市中給我們讀他的小說時,當時那可是『熱門的話題』,卻讓我們時常有一種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覺。他竟然這麼快就利用這些題材做文章,而且處理得如此順暢。成千上萬的人在我們身邊受盡折磨致死,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如此迅速地轉化為悲慘的戲劇場面,這樣做,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不成體統。」這裡指的是,對於那些身體還未涼透的人們,要有一種敬畏和距離,而不是馬上給他們塗上胭脂。寧願站在沉默一邊,也不要站在喧譁一邊。寧願失語,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肅穆的感覺,更不要馬上去學會強權者的語言和腔調。
書中《波羅的海》這一章,他發出一生中少有的尖銳批評。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內波羅的海三國再次被紅軍占領,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謂「強化農村階級鬥爭」的,使得戰後擁有散落武器的人們逃進森林,組織武裝隊伍進行反抗。結果是更多的人被裝進悶罐車,被送往人煙稀少的地方。「他們身後留下了空無人跡、反覆受到劫掠的村莊,風在破碎的窗戶與撞開的門上呼嘯而過」。這時候西歐人開始享受平緩的和平生活,沒有人注意這一切。東方和西方的輿論沒有人關注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著的一封信,它來自原先生活在波羅的海的一個家庭,一家三口母親與兩個女兒,於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信中以乾巴巴的簡短語言敘述了她們在集體農莊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後一個字母都很粗,將它們連在一起看,就出現了「永恆的奴隸」這個字樣。這是被抹殺中一聲悲苦的叫喊。米沃什從中想到了「還會有多少人想寫信卻沒有寫出來?還有多少可能會寫這種信的人,因飢餓和過度勞累死於冷酷的北極地區,死時仍然在不斷重複這句令人絕望的話『永恆的奴隸』?」
炫耀的強權與被沉埋的人們在詩人身上進行拉鋸,就像曾經不同的力量在爭奪和分割他的家鄉,他的祖國。他自己經歷的下面這個故事,同樣體現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個夜晚,作為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參加一個聚會,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點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涼,他看到了幾輛滿載著犯人的吉普車。在場計程車兵和守衛穿著兩層的軍大衣,而那些囚犯們身穿夾克,凍得渾身哆嗦。「那時我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凶」。
米沃什決定停下來了,他不能再跟著時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將「人」和「歷史」對立起來,經過遲疑鬥爭,米沃什最終選擇了「人」:具體的、生活在某處的人們,有著熟悉親切的面龐。他決定背負來自出身地的無邊苦難,承擔那些永遠沉埋地下的人們的痛苦。他選擇站在了失敗者一邊:「我是站在未來的勝利還是被戰勝的人一邊,我的將來是贏還是輸,全都無所謂。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將嘗到甜美的勝利果實,如果地球經過長達數百年計劃經營而得到改造,對能活到那個時候的人來說將是極大的悲哀。」這幾句話表明,米沃什同樣擁有奧威爾那樣的預言能力。這種能力並不神秘,是一個藝術家對於人類事務的關心,所擁有的穿透性目光。後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他說得對。
實際上,這個世界在任何情況下都同時顯出兩副面孔:一方面是華美的和歡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這是米沃什寫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詩《菲奧里廣場》,其中一邊是在美好歡笑中度周末的人們,不遠處的另一邊便是猶太區著火的房屋、被風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對於後者全然沒有感覺。然而,暴力正是在人們的忽視中開始變得流行,悲劇在人們的輕率中一件接著一件發生。
一個晴朗的春夜
在華沙按狂歡的曲調
旋轉木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奧里
興高采烈的旋律淹沒了
猶太區屋牆傳來的炮彈齊發聲
雙雙對對高飛
在無雲的天空
有時從火堆吹來的風
把黑色風箏吹過去
旋轉木馬的騎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陣熱風
還吹開了姑娘們的裙
人們開懷大笑
在那美麗的華沙的星期天
(綠原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