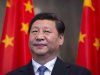作者:張謳
來源:網絡
我於1988年留學英國。當時,《1984》的熱度仍未減弱。我在一家舊書店裡買了一本。這是我首次接觸奧威爾的作品。書中細節殘忍驚悚,又如此熟悉。
在奧威爾筆下的大洋國里,老大哥靠著兩手來維持統治:一是製造對外仇恨,自己遇到困難時,就聲稱敵人在背後搗亂,讓民眾生活在這種仇恨之中。這樣才能保住統治者的地位。另一手就是銷毀真實的歷史記錄,以此來證明自己永遠正確。遇到質疑者,就用恐嚇來進行「思想教育」。
大洋國倡導「新話」,通過減少詞彙和含義,進而簡化國民的思維方式。在人類社會演變中,語言一直是思想的載體,是含有胚芽的種子。一旦政治高溫燙死胚芽後,種子便成了殭屍。獨裁國家的生存法則是:形式即內容,服從即熱愛,權力即秩序。
一、倫敦擁有最多的奧威爾紀念標誌
奧威爾去世前,其作品已經廣受好評。由於他的政治預言尚未被證實,其影響力尚未被廣泛認知。
奧威爾於1950年1月21日去世。根據其遺言,奧威爾希望按照聖公會的告別儀式舉行葬禮,然後埋葬在教會公墓里。雖說他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在印度比哈爾邦的聖約翰教堂接受了洗禮,其祖父曾是牧師,但是奧威爾長大成人後,幾乎沒有參加過教會活動,因而沒有教區牧師肯接納他。
奧威爾有一位好友叫戴維·阿斯特。他原打算把奧威爾安葬在克萊夫登。那裡有阿斯特的家族莊園,阿斯特的母親還是英國首位女議員。當地的教堂牧師拒絕了他的請求,認為奧威爾不是虔誠的基督徒。
阿斯特又來到牛津郡的薩頓考特尼村。他家在那裡也有房產,自己也經常參加教堂活動。他找到了戈登·鄧斯坦牧師。牧師表示同意,又說,還需要徵求公墓管理員的意見。一位管理員表示反對。鄧斯坦牧師從兜里掏出《動物農場》,說要安葬的是此書作者。那位管理員點頭同意。
奧威爾的遺體告別儀式於1月26日舉行,地點是倫敦阿爾巴尼街的基督堂。只有奧威爾的親友和出版商到場。告別儀式結束後,殯儀人員把奧威爾的加長棺材運了過來。現場只有戴維·阿斯特、奧威爾的遺孀和律師,場面冷清。他們看著奧威爾的棺材緩緩放入墓穴中。

本文作者在喬治·歐威爾墓地
奧威爾的墓碑平實樸素。或許是泥土塌陷的緣故,石碑有些傾斜,上面刻著奧威爾的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萊爾安葬於此,生於1903年6月25日,卒於1950年1月21日。」
20世紀末,奧威爾的政治預言得到了驗證。這不僅確立了奧威爾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中的獨特地位,也受到了民眾的擁戴。他生活過的地方,從印度比哈爾邦到緬甸,從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到英國各地,都有了各式各樣的紀念標誌。
1980年,由「大倫敦議會」批准的官方藍色牌,釘在了奧威爾曾經居住的倫敦勞福德路的灰磚牆上。從1935年8月至1936年1月,奧威爾與兩位文學青年在這裡合租了一層公寓。奧威爾在此完成了《讓葉蘭搖曳不停》一書。葉蘭是倫敦室內最常見的綠植,生命力頑強。他於1936年初離開此地,前往北方調查產業工人的生存狀況,後來完成了《通往威根碼頭之路》。
這種帶有「大倫敦議會」字眼的藍牌,是倫敦最高規格的紀念牌,用以紀念那些曾經居住在倫敦、為英國和人類社會做出重要貢獻的名人。此活動始於1866年,有嚴格的審核程序。凡是被掛上藍牌的建築,均被列入受保護的「英國遺產」。居住者不得隨意裝修或改變外形。

奧威爾租住在倫敦波特貝羅路的聯排公寓
奧威爾最先租住在波特貝羅路的一棟聯排公寓,當地社區也製作了一塊藍牌,釘在外牆上。奧威爾於1934年至1935年初曾在漢普斯泰德的愛書角書店工作,那棟建築現在是蓋爾烘焙店,店主在外牆上鑲嵌上了奧威爾塑像。奧威爾夫婦於1944年居住在卡農伯雷廣場27號B室,他在那裡完成了《動物農場》。卡農伯雷社區也鑲嵌了一塊綠色紀念牌。
奧威爾愛去倫敦酒吧,還在1946年寫了《水中月》一文,發表在2月9日的《旗幟晚報》上。他虛構了一個「水中月」酒吧,描繪了英國酒吧的美好。康普頓酒吧(Compton Arms)、菲茨羅伊酒館(Fitzroy Tavern)都宣稱,奧威爾是他們酒吧的常客。附近的麥束酒吧(Wheatsheaf)在外牆上釘上一塊奧威爾紀念牌。紐曼酒吧(Newman Arms)聲稱,奧威爾不僅來這裡喝酒,還經常與文學編輯在酒吧里討論稿件。
二、從印度到緬甸
1903年6月25日,奧威爾出生在印度比哈爾邦的莫蒂哈里(Motihari),本名是埃里克·亞瑟·布萊爾。他父親理察·布萊爾在英印政府的鴉片部任職。在英國的海外殖民地中,英屬印度匯集了最多的英國專業人才。很多英國名人的前輩都曾在印度工作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出生在孟買。計算機之父圖靈的父親和祖父都是英屬印度官員。
我在印度工作期間,曾探訪了埃里克的出生地。那裡只剩下了破敗的紅磚平房,牆體上有幾個大窟窿,幾隻羊在院子裡吃草。這種平房稱為bungalow,即孟加拉風格的平房。這種帶有傾斜屋頂的單層建築,具有通風透氣的特點。
在印度文學界的呼籲下,布萊爾家的房屋依據《文物法》被保護了起來,卻遲遲未能修繕,房屋幾近坍塌。直到2014年,比哈爾邦的東查帕蘭行政區才進行了修復。其故居現在已經對外開放。埃里克最早的照片就拍攝於此。印度奶媽抱著埃里克,埃里克向後仰頭,用手抓著奶媽的紗麗。
埃里克1歲時,母親把他帶回英格蘭。母親是英法混血兒,祖輩在緬甸經營木材生意。她從緬甸去印度謀生後,與布萊爾結為伉儷。埃里克的父親在55歲時退休,回到了英格蘭。父母時常聊起印度。這種懷舊式交流,逐漸讓埃里克與印度有了情感連結。

奧威爾在印度的出生地
這種情感連結讓埃里克一直關注著印度局勢。當廣播和報紙中出現「印度」字眼時,他都會格外留心。1947年8月15日,聖雄甘地倡導的「不合作運動」,讓印度贏得了獨立。奧威爾一直在思考,假如英國殖民者採用史達林的統治模式,結局會是怎樣?
他在《甘地沉思錄》(1949年1月)中寫道:「甘地畢竟生於1869年,他不懂得極權主義的性質,他在用與英國政府的鬥爭經驗來看待一切事物……在一個反對現政權的人在午夜說消失就消失、從此銷聲匿跡的國家裡,採用甘地的抗爭方式難以想像。沒有新聞自由和集會權利,僅僅呼籲外國輿論的關注,甘地的方式行不通,更遑論組織群眾運動,乃至讓當權者理解你的意圖了。現在,俄羅斯有甘地式的人物嗎?如果有的話,他幹了些啥呢?」
作者有如此深邃犀利的觀點,是他從自己的經歷與政治觀察中得來的。
到了入學年齡,母親把埃里克送到了薩塞克斯郡的聖塞普里安學校。這是一所寄宿學校。學生主要來自中產以上家庭。埃里克一直是優等生。他由此榮獲了伊頓公學的國王獎學金,由此進入了伊頓公學。伊頓公學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精神。通過各類體育競賽,強化了伊頓學生們的獨特氣質。
埃里克從伊頓公學畢業後,未升入大學。布萊爾夫婦在遺憾之餘,又希望兒子效力於英屬印度。埃里克在1922年6月通過了考試,四個月後就乘船前往緬甸,成了一名緬甸警察。
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前往東方淘金。獲取財富的手段就是通商。如果拒絕通商,那就用槍炮打開對方的國門。英國東印度公司後來居上,通過武力征服和簽署契約,逐漸獲得了印度的控制權。英印軍隊與緬甸進行了三次戰爭,緬甸逐漸淪為了英國殖民地。緬甸於1948年1月4日宣布獨立。自己當家作主了,緬甸經濟卻從亞洲富豪榜上,一路走低,淪為最不已開發國家。
20年前,我持中國護照,從印度進入緬甸仰光。過關時,海關人員得知我的記者身份後,立刻變得警惕起來,反覆問我來緬甸幹什麼,是否得到了緬甸新聞部門的批准。我說自己只是來旅遊的。與我同行的印度記者,則沒有那麼麻煩,海關人員麻溜地蓋章放行。同為緬甸的鄰國,緬甸人實際上是區別對待的。這種區別對待,只能在比較中才能體會到。
外國遊客到了緬甸後,要詳細填寫自己的信息。客棧老闆說,這些信息都要向當地警察局報備。我的第一站是仰光,那裡擁有東南亞最大規模的英式建築。當我對著政府大樓拍照時,警察用英語大喊:「No Photo!」我也大聲喊:「No Photo,Please」。這反倒把警察搞懵了。我在印度工作多年,自有一套對付警察的方法。
我讀過英國人寫的緬甸遊記。當我來到緬甸後,卻發現很多地名都變了。同印度的情況一樣,本國政治家都認為,更換殖民地時期的地名,就是在洗刷一段恥辱歷史。名字本身所包含的一段歷史信息,也被一同抹掉了。緬甸的英語名字從Burma改為Myanmar。全世界的地圖也必須跟著更改。
我從仰光乘坐公共汽車抵達曼德勒,遊覽了一天,又乘火車抵達納巴(Naba)。這條鐵路線是英國人在1910年鋪設的。從納巴到奧威爾曾經工作的卡沙(Katha),還需要乘坐計程車。卡沙是地區行政總部所在地。英國人當年建造的醫院、學校仍在使用,仍是當地的標誌性建築。
埃里克來到緬甸後,先在曼德勒警察學校接受培訓,還學習了緬甸語和印地語,畢業後被分派到了最艱苦地區。這是英國警察培育後備力量的傳統方式。埃里克最後來到了卡沙。
《緬甸歲月》就是以卡沙為背景完成的。從卡沙旅遊地圖上,很容易就能找到英國人留下的建築,如俱樂部、網球場,醫院和警察局等。它們都是種族身份的象徵。奧威爾曾經住過的老房子,是一棟紅磚房、鐵皮屋頂,還有柚木窗戶。小說中的歐洲人俱樂部,是一座英國與緬甸建築的混合體。一樓是水泥澆築,二層是柚木牆體。兩層建築都有誇張的屋檐,用來遮擋熾熱的陽光和暴雨。
緬甸卡沙的英國人俱樂部
《緬甸歲月》比《巴黎倫敦落魄記》晚一年出版。從《巴黎倫敦落魄記》開始,埃里克使用了筆名喬治·歐威爾。當時的英國國王是喬治五世。作者取此名字,或許是想表明自己生活在喬治時代。奧威爾則是家鄉河流的名字。奧威爾的早期作品帶有濃厚的自傳風格。這避免了有人在作品中對號入座,也可以屏蔽掉自己家族的殖民地背景。
我曾與一位緬甸記者討論過《緬甸歲月》。他說,「奧威爾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緬甸,把緬甸人描寫成喜歡投機鑽營的貪婪者。這是不能接受的。」我當然不同意這種說法。奧威爾實際上譴責的是社會體制,而非緬甸人。好體制可以讓鬼變成人,壞體制則讓人變成鬼,強化了人性中的醜惡。
奧威爾從小就被灌輸了一種觀念: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是正當的。奧威爾自己也承認,英國人在管理方面比緬甸人更出色,但是種族歧視無處不在,而且殖民者濫施刑罰。奧威爾對自己參與其中深感自責。當他患上了登革熱後,便申請回國休假。警察總局批准了半特休期。他在休假期滿前遞交了辭職信。這讓他失去了帶薪休假的資格。
奧威爾由此開始了自己的流浪人生。他穿著破舊的衣服,圍著一條圍巾。無論天氣多麼寒冷,他從不穿大衣。他主動沉入社會底層,記錄自己與各類人的交往。他在巴黎餐館洗盤子,打零工,在倫敦的萊姆豪斯與流浪漢混在一起。生活越困頓,他的思維越靈敏。其記憶猶如磁鐵,連生活中的瑣碎細屑都能吸附上來。這成就了奧威爾早期作品的「紀實風格」。
奧威爾是蘇格蘭人後裔,卻自幼生活在英格蘭。他身上既有蘇格蘭人的性格特點:執拗、嚴厲、崇尚強悍和精神苦行,也有英格蘭人的特徵,如堅持自由和契約理念;注重個人尊嚴,又喜歡自嘲。當時倫敦是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這讓倫敦人「自負又傲慢」。奧威爾看不慣這種風氣。他在文章中諷刺道:倫敦人總認為倫敦是地球的中心,所謂中心,大概就像「肚皮是人體的中心一樣。」奧威爾的諷刺頗有特色,既能刺痛對方,還能讓對方捂著嘴樂。
無論如何挖苦和諷刺英國,奧威爾仍認為自己是英國的一員,十分在乎自己的國家文化。奧威爾寫道:「更重要的一點是,它是你的文化,它是你,不管你何等地憎惡或是嘲笑它,一旦離開它哪怕片刻,你都不會感到快樂。」
二、西班牙內戰讓他認清了極權本質
真正讓奧威爾發生思想巨變的,是西班牙左翼組織的派系鬥爭和史達林式的政治清洗。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7月18日爆發,奧威爾一直關注著西班牙的局勢。當年12月初,奧威爾把《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書稿寄給了格蘭茨出版公司,拿到了100英鎊的出版預付款,自己還籌措資金,準備參加反佛朗哥的左翼陣營中。
在倫敦的國王大道,奧威爾見到了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里特,卻沒有拿到介紹信。他只得求助於獨立工黨。獨立工黨把奧威爾介紹給了巴塞隆納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簡稱馬統工黨(POUM)。這是一個「奉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先鋒黨。
奧威爾沒有來得及過聖誕節,就轉道巴黎來到了巴塞隆納。一位加泰隆尼亞記者陪同奧威爾,視察了6個月前發生暴亂的街道。樓頂上飄揚著代表不同黨派的彩旗。「幾乎每一所教堂都遭到洗劫,聖像被焚燒,各處的教會建築統統被拆毀;每一間店鋪和咖啡館都掛出了告示,聲明已歸集體所有;甚至連擦鞋匠們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被塗成了紅黑兩色。」
奧威爾參加了該黨的民兵組織。他們的武器是1896年德國產的毛瑟槍,鏽跡斑斑,缺少零配件。奧威爾在巴塞隆納培訓了7天,就被派到了東北前線。奧威爾承認這支隊伍缺乏訓練。部隊中的很多傷員,幾乎都是被自己的槍彈誤傷的。
1937年2月,奧威爾的妻子愛琳來到了巴塞隆納。他們兩個於1935年3月在倫敦相識。艾琳畢業於牛津大學,當時正在倫敦大學學院攻讀教育心理學碩士學位。倆人訂婚後不久,就一起回到了赫特福德郡的沃靈頓,於1936年6月9日在聖瑪麗教堂舉行了婚禮。
奧威爾與艾琳在此教堂舉行婚禮
艾琳來到巴塞隆納後,在獨立工黨的辦事處謀得一份差事。3月中旬,她被許可去前線探望丈夫,在那裡逗留了3天。戰場上沒有大規模軍事對抗,多為偷襲和局部衝突。
奧維爾在4月份回到巴塞羅納休整,卻發現那裡的政治空氣變得詭異,不同派別之間爆發了巷戰。這讓奧威爾感到厭惡。他認為,左翼陣營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對付敵人。奧威爾又返回了戰場。
5月20日,在阿拉貢前線,敵方射來的一顆子彈,擊中了剛剛換崗的奧威爾。眼前閃過一道炫光,他頓時失去了知覺,緊接著被送到了戰地醫院。醫生檢查後發現,子彈從他的氣管與頸動脈之間穿過,他不可能參戰了,於是就轉到了統一工黨管轄的莫林療養院。
奧威爾於6月中旬從醫院康復出來後,妻子告訴他,馬統工黨已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六名便衣警察曾進入奧威爾妻子的房間,搜走了書籍和剪報。奧威爾在前線時,曾在廢紙和信封背面記下戰況和感想,也一同被搜走了。
一位英國學者告訴我,蘇聯秘密警察幾乎跟蹤調查過所有的國際志願者。莫斯科黨中央檔案館至今保持著布萊爾夫婦的政治鑑定,稱倆人是「狂熱的托派分子」。埃里克·布萊爾是個小說家,寫過幾本關於英國無產階級生活的書,政治覺悟低。
奧威爾長期生活在英國,即使在緬甸,也從未經歷如此殘酷的內鬥和政治迫害。西班牙左翼陣線有八個黨派。早在1936年12月,史達林就下達指示,讓西班牙蘇維埃內務部秘密警察除掉馬統工黨,原因是該黨書記安德烈與托洛茨基曾有聯繫。蘇聯大清洗始於1935年,史達林指使秘密警察,處決和流放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巴塞隆納的左翼陣營也採用了蘇聯套路,進行非法審判和處決。統一工黨領袖被投入監獄,一些英國志願者也病死在獄中。
這種政治迫害讓奧威爾感到心寒。他決定帶著妻子回國。在離開巴塞隆納的前夜,奧威爾躲在教堂廢墟里。他第一次仔細觀看了高迪設計建造的聖家族教堂。這是少數幾座未被毀壞的教堂之一。第二天,奧威爾和妻子裝扮成英國遊客,登上了去法國的火車。他們在中途逃過了特務檢查,才進入了法國境內。
我曾經多次到訪過巴塞隆納。奧威爾提到的拉布拉斯大道(Las Ramblas),仍是當地最有名的觀光之地。寬敞的大道兩側是商店,中間是行人徒步區。遊客和當地人坐在商店旁的座椅上,圍著桌子聊天喝酒,吃幾片薄得透明的豬腿肉,再加上一盤沙拉,裡面拌上橄欖油、葡萄釀製的醋,就會聊上半天,他們的肢體動作豐富。大道的一端盡頭就是地中海的港灣,直入雲霄的紀念柱上是哥倫布雕像。

巴塞隆納的喬治·歐威爾廣場
在巴塞隆納哥特區,有一座以奧威爾名字命名的小廣場。這裡空間狹窄,曾是醉鬼們酗酒鬧事之地。1996年,巴塞隆納市議會把此地命名為喬治·歐威爾廣場,由此吸引了很多外國遊客,這裡的環境也有了明顯改善。我問當地居民關於西班牙內戰的事,大多數人都說不記得了。當地人最愛談足球和性,熱衷貶低馬德里的政治領袖。望著天空中浮動的白雲,我反倒有些恍惚起來。
三、在倫敦的日子
從巴塞隆納回來後,奧威爾撰寫了幾篇揭露西班牙左翼內鬥的文章,卻遭到了左翼雜誌的封殺。幾乎所有的左翼雜誌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只服務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視自己的信仰為真理,不接受任何質疑。好在英國有言論自由。此家不刊登,那就選擇另一家。
1937年下半年,奧威爾帶著妻子回到了沃靈頓村,租下了一座帶販賣部的農舍。每周租金是7先令6便士,夫妻倆在農舍旁開闢了菜園,飼養家禽。倆人在販賣部出售香菸、土豆等日常生活用品,收益基本可以支付農舍租金。

奧威爾在赫特福德郡沃靈頓的故居
在鄉村環境中,奧威爾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埋頭撰寫《致敬加泰隆尼亞》。戰場上腐爛的氣味兒、街道上刺耳的口號和噪音,都清晰地呈現了出來。他在《我為何寫作》中說:「自1936年後,我寫下的嚴肅作品中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反對獨裁主義,支持我心目中的民主社會主義。」這段話成了解讀奧威爾後期作品的一把鑰匙。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9月1日爆發。兩天後,英國正式向德國宣戰。從1940年7月到1941年9月,德國執行了迫使英國屈服的「海獅計劃」,共出動了飛機4.6萬多架次,向英國投下了7萬多噸炸彈。這反倒激發了英國人更頑強的鬥志。奧威爾堅持住在倫敦,撰寫了多篇戰時隨筆。
1941年8月,奧威爾應聘到了BBC,成為了印度分部的談話製作人。奧威爾把廣播稿寫得流暢自然,但是播音時,由於他的嗓子受過槍傷,聲音顯得枯燥和單調。那種聲色並不能吸引聽眾。時間一長,奧威爾對這種宣傳效果產生了懷疑。1943年9月24日,奧威爾辭去了BBC的工作,開始擔任《論壇報》的文學編輯。
在擔任文學編輯期間,奧威爾開始創作《動物農場》,並於1944年2月完稿。在這部寓言小說中,一群動物完成了「暴力革命」,建立了一個看似平等的動物社會。狡猾的豬卻篡奪了勝利果實,開始了比人類更冷酷的極權統治。「一切動物生來平等,有些動物卻享有更高的平等。」小說中的這句話,成了廣為人知的名言。
這部寓言小說明顯是在影射史達林的統治,如強制推行集體化經濟,誣陷政治對手,排除異己等。在二戰期間,蘇聯和英國屬於同盟國,正在共同對付德國納粹。奧威爾先後找了五家出版公司。老闆們都認為,戰時出版此書不合時宜,有可能在同盟國之間造成裂痕。
英國活躍著各種思想,這是國家強大生命力的體現。塞克爾和沃伯格出版公司捕手了這部書稿,並於1945年8月出版。小說出版不到一個月,二戰宣告結束。讀者從這部寓言小說中,看清楚了獨裁者的真面目。歐洲國家很快有了八個譯本。
奧威爾與艾琳沒有生育孩子。他們從醫院抱養了一個棄嬰,取名理察·霍雷肖·布萊爾。1945年初,醫生發現艾琳的子宮裡長了腫瘤,手術定於3月29日。當時奧威爾正在應《觀察家》和《曼徹斯特晚報》之邀,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在法國報導戰況。兩天後,39歲的妻子卻死於術前麻醉。
奧威爾從巴黎趕了回來,心情極其沮喪。他不僅記錄了眾生的苦難,他自己就是苦難的一部分。艾琳婚後一直跟隨著他,吃盡了苦頭。《動物農場》為奧威爾帶來了豐厚版稅。他們的生活剛有起色,妻子卻撒手離開了。
四、在蘇格蘭朱拉島上
奧威爾早已習慣了邊緣人的生活。當《動物農場》把他帶到社會聚光燈下時,他反而變得不自在。如果繼續留在倫敦,他只能應付源源不斷的報刊約稿,參加各種累人的社交活動。他還想集中精力,完成一部更有力度的長篇小說。
奧威爾在1940年就提到了赫布里底群島,期待在那裡生活。經過一番考察,奧威爾選中了朱拉島。那裡僻靜又隱蔽。他租下了島上最北側的巴恩希爾(Barnhill),意為「谷丘」。房主羅賓·弗萊徹曾是伊頓公學的舍監。奧威爾托人把房子粉刷了一遍,添置了幾件家具。
從奧威爾時期到現在,進出朱拉島都不容易。我先乘坐CityLink抵達肯納克雷格,後面便是奧威爾當年的行走路線。到了朱拉島後,乘車到阿德魯薩村,再走上7公里的土路,才能來到奧威爾故居。
巴恩希爾基本保持著當年的原貌。其產權仍屬於弗萊徹家族。客廳、廚房和餐廳都在一樓,牆上掛著老舊的歐洲地圖。我踩著吱吱作響的樓梯上到二層。上面有四個臥室。其中一間臥室的窗台前放著一張木桌,上面有一台打字機。
朱拉島上的奧威爾故居
1947年初,奧威爾解除了沃靈頓農舍的租約,於4月份來到了朱拉島。幾個月後,奧威爾把保姆蘇珊·沃森和養子理察從倫敦接了過來,自己的妹妹阿芙麗爾也來到了這裡。奧威爾和家人在附近的海礁上捕魚,在沼澤地旁邊開闢了一片菜地。
奧威爾開始創作醞釀已久的長篇小說。荒涼的孤島符合小說的基調,代表精神孤獨和壓抑。小說中的故事卻是在城市裡展開的。奧威爾就把自己熟悉的倫敦街景搬進了小說里。真理部原型是倫敦大學理事會大廈。這座大廈是戰時的信息部總部。他妻子艾琳曾在那裡工作。勝利廣場就是特拉法加廣場。這種似是而非的背景,遠勝於虛構出來的世界。
朱拉島的濕冷天氣,導致奧威爾的支氣管炎發作。1947年12月20日,他住進了格拉斯哥南面的海爾默雷斯醫院,被確診為肺結核。醫生採用的是隔膜擠壓法。奧威爾把那種痛苦感受,用在了小說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身上。
溫斯頓不滿黨控制一切的社會體制,結果被秘密警察識破。他被逮捕入獄,連續遭受酷刑,「腿上一直感覺虛弱,膝蓋疼痛。僵硬感發展成腰背和下方的疼痛。」經過懲罰後,溫斯頓最終相信了黨的絕對真理,即二加二等於五。他突然覺得黨組織對自己的關懷勝過母親,哪怕黨代表奧布賴恩少看他一眼,他都感到恐慌不安。他隨時準備犧牲自己來捍衛黨的利益。
1948年7月28日,奧威爾回到了朱拉島。他經常穿著睡衣,靠在鐵床架上寫作。這讓他的字跡潦草,以至於找不到一位打字員來幫他列印書稿。他只好自己用打字機,敲打出了整本書。書稿於1948年11月完成時。他把1948年的最後兩位數字顛倒過來,成了這本小說的書名。
出版商沃伯格拿到《1984》的定稿後,立刻排版印刷出來。他對奧威爾說,幾位書店老闆讀了新書樣本後,竟嚇得整晚無法入睡。
二戰結束後,世界冷戰的序幕已經拉開。《1984》的出版,可謂正逢其時,引起了歐美讀者的熱烈反響。美國把《1984》當作反蘇教材,奧威爾則一再強調,這是一部反極權主義的作品,而非其它。
在完成《1984》後,奧威爾開始咳血,他一直拖到1949年1月份,才離開了朱拉島,前往科茨沃爾德療養院。奧威爾又有了新的寫作計劃。此時,他認為再婚有利於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他與索尼婭·布勞內爾相識多年,索尼婭比奧威爾小15歲。這種「病床上的愛情」一度引發了各種猜測。到了9月初,奧威爾的病情不見好轉,他被轉到了倫敦大學學院附屬醫院,住進了65號病房。10月13日,奧威爾與索尼婭在病房裡舉行了婚禮。
奧威爾的心情變得愉快。他妹妹帶著5歲的理察,從朱拉島趕來探望奧威爾。奧威爾滿眼溫柔和愛戀,甚至計劃全家去瑞士旅遊。1950年1月18日,奧威爾突然感到呼吸困難。他叫來了律師,寫下了遺囑。1月21日凌晨,奧威爾肺內的一條血管破裂,導致大量出血。他無力按下呼叫鈴,索尼婭當時也不在身邊。等到護士來查房時,奧威爾已經去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宿命。隨著時間的推移,奧威爾作品的鋒芒漸顯。英國首相邱吉爾把《1984》讀了兩遍,還推薦給了自己的朋友。到了1989年末,這部作品又進入了歐美暢銷書排行榜。
奧威爾不僅是著名作家,也是出色的記者。21世紀初,BBC建造了新的廣播大樓,大樓外側豎起了奧威爾的全身立像。奧威爾曾批評過BBC的管理模式。他在辭職信中寫道:「我很清楚,自己是在無效的工作上浪費時間和公共錢財。」 BBC並不因為這種批評而疏遠奧威爾,仍把他視為新聞記者的楷模,敢說真話、直面生活。這正是英國精神的體現。

BBC大樓前的奧威爾全身立像
奧威爾立像旁邊鐫刻著他寫的一句話。這句話原本出自《動物農場》的序言。由於當時紙張嚴重短缺,出版商刪掉了這篇序言。這篇序言已被收入倫敦大學學院的奧威爾檔案中。
《動物農場》序言中的這個句子是:「如果自由意味著什麼的話,那就意味著有權利把民眾不想聽的告訴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