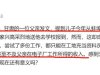一
父親一生歷盡艱辛,就是為了這些吧。他堅毅果敢,家國是心頭首要的責任。記得小學三年級一天的晚飯後,他把我們兄妹三人叫到跟前,讓我們都在他對面坐下來,然後喝了一口濃茶,嗽了一下嗓子說:「你們也不小了,有一件事應該讓你們知道,今天和你們說吧。」
我們都緊張起來,父親從未和我們如此鄭重地談過話。
他說,他曾經兩次和死神擦肩而過。有一次飛行中突然遇到狂風和氣流,飛機就像一片小樹葉,被狂風裹挾著以最快的速度向一座雪山山峰撞去,眼看著峭壁瞬間衝到了眼前,他嚇得頭皮發炸雙眼暴突,拼死命拉操縱杆,滿載抗日物資的飛機咆哮嘶吼著終於升高,逃過了這一劫。
還有一次,那天怎麼就發起高燒來了?42度多,渾身滾燙視力模糊,頭暈眼花走路踉蹌,怎麼能夠值班去飛行呢?本來,父親他們是絕不能請假的,因每一次飛行都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後一次絕飛,誰該來代替你呢?但是一位年輕的美國飛行報務員站了出來,代替父親值班。也就是在那天傍晚傳來噩耗,那架滿載抗日物資的C-47運輸機失事,在茫茫雪山中消失,後來知道,三位美國飛行員全部遇難……
父親說,如果那天不是他發高燒,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他,也就沒有我們了……
「為什麼是美國飛行員?你為什麼和美國人一起飛行?在哪兒飛?那是什麼地方?」我不甘心地問。那是個仇恨美帝國主義的時代,我根本不相信美國鬼子會幫助中華民族抗日。父親愣了一會兒,欲言又止,嘆了口氣,不再說這件事。
他又說,1949年11月9日,自己從香港參加了兩航起義,他和35位飛行員一起,滿懷赤子之心,駕駛著12架飛機冒著生命危險回到了大陸。這12架飛機,和後來由兩航人員修復的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16架飛機,構成了新中國民航初期的機群主體。在他們之後,四千多位兩航職工全部起義,回到了大陸。「你們媽媽抱著萬城(在香港出生的哥哥)後來坐輪船回來,好險啊,下船後才發現,行李被偷走了一大半!那些很多都是金銀細軟呀!」。
父親還告訴我們,就這樣,他還是把家中的全部存款都捐了。
「存款都捐了?捐給哪兒了?」哥哥問。
「1951年,國家號召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我都沒和你們媽媽商量,就把全部存款捐給了國家。」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總會發出《關於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軍屬的號召》後,到1951年12月27日結束捐款,全國人民已經捐了47280億元(舊幣),可購買戰鬥機3152架。
母親說,當時在報紙的一個小角刊登過父親捐款的消息和數額,可惜這報紙已找不到了。

兩航起義人員抵達天津,第一排右三是我父親
父親的兩次死裡逃生,似乎和我們很遠,他現在不是還活著嗎。他的捐款好像和我們也沒關係,小小年紀,對錢沒有概念。
單純率真的父親毫不懷疑自己豐厚的工資足夠養活一家五口。他無論如何想不到,多舛的命運已經像一張巨大的黑傘,遮住了陽光和希望。幾年後就削減工資100多元,幾年後又減了一百多元,回國不到十年,不愁衣食的生活已經成為了歷史。
記得一次他下班回家,愁容滿面地對母親說:「我工資又減了,現在一個月……只有109元了。」母親驚愕得瞪大了眼睛,半晌才帶著哭腔說:「我們怎麼活呀……」
後來,幾乎每個月都入不敷出。我經常看到他們愁容滿面地拿著記帳本一點點地算,什麼地方還可以再省一點兒?在香港時家境優越,家中有廚師保姆,哥哥有奶媽。面對現在的狀況,父母不知該如何節省,更不知如何適應北方的生活。母親是穿著旗袍和高跟鞋回來的,她能做畫,能彈琴,說一口流利英文。她既是摩登女郎又是嫻靜淑女。家境優越的她連饅頭都沒見過,以為吃時要剝皮。現在,需要自己生爐子,自己做衣服,還要學會給我們理髮剪髮。每分錢都得算計,都要節省。就這樣仍舊不到月底就捉襟見肘,只能向親戚借錢或變賣東西。但無論怎樣拮据,過年時母親肯定會讓我們穿上新衣服。
二
1960年「自然災害」時患心臟病的弟弟做了心臟大手術,出院後卻無法給他補養身體,不要說肉,已經很多天連蔬菜都吃不上了。母親向鄰居學著,把淘米水留下來沉澱,最後那些底部渾濁的米粉還可以熬出糊糊,給我們吃。後來聽說鼓樓後面有個「黑市」,也就是「地下」農貿市場,因當時沒有個體經濟,任何出售私人產品或物品的行為都是犯罪,賣東西的地方就是「黑」市。母親叫哥哥到那裡去小心找找,希望能買到一點兒蔬菜給弟弟吃。哥哥去了之後,不知運用什麼火眼金睛還真的就買到了一顆小小的白菜,裹在衣服里興高采烈地回來了!
那棵白菜的樣子我記得非常清楚,長度是5、6寸,直徑2寸左右,我們放到鼻子底下深深地聞,好香好香的蔬菜味兒!這棵白菜花了整整1元錢,是全家兩天的生活費。白菜給弟弟吃了,那個白菜根可捨不得扔,我把它養在一個漂亮的小碟里,放在窗台上。它居然又慢慢長出了幾片綠油油的葉子,在陽光下舒展婀娜身姿,為全家帶來了快樂和維生素。
我六歲開始學鋼琴,那個時代的小學生童年都是玩兒過來的,跳皮筋、扔包,歘拐(歘讀chua,三聲,舊時北方小女孩的玩具,是羊的膝蓋骨,只有後腿有),樂此不疲。我卻很像現在的小學生,放學後從沒有時間玩兒,坐在鋼琴前一遍遍地彈奏練習曲,星期天也不得休息,要到少年宮去參加舞蹈組和合唱團的活動。父母還讓哥哥學小提琴,弟弟學長笛。他們希望從小培養我們一些音樂素養,能夠接受豐沛的教育,並嚴格要求我們的品格高貴,豐富,質潔。
但日子卻越來越艱難。1961年的一天晚上,我竟然聽到父母商量著要把鋼琴賣掉,補貼家用。我傷心欲絕,趴在鋼琴上哭了很久。雖然我彈練習曲的時候有時偷看小人書,雖然我心煩的時候彈了五遍就會騙媽媽說彈了十遍,但還是深深地愛上了這能迸發生命熱度的黑白琴鍵。
淚水無法阻止父母的決心,那天,幾個身材高大的工人來搬鋼琴了。我大哭著向父母哀求,我可以不吃糖,不穿新衣服,請你們不要賣掉鋼琴……但是,放鋼琴的地方已經變成了一塊黑色的空淵。我站在那裡,眼神呆滯,很久才清醒過來。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巨大悲哀。就這樣,父親也絕不後悔自己當初捐出了全部存款。
鋼琴買的時候1250元,四年後只賣了400元。這鋼琴變成了我們兄妹三人長身體急需的魚肝油和蛋白質。兩年後哥哥考上了北京五中,1965年,我雙百分考上了清華附中。

七歲的我在彈鋼琴
三
初一還沒有讀完,那天就來了。
怎麼會有這樣顛倒黑白的日子?怎麼對國家,對民族危亡用自己生命承擔的父親,被民航革委會定為「特務、間諜」,成了階級敵人?小小的我,怎麼就成了狗崽子?
國人就像被注射了生化毒素,相互之間發起匪夷所思的毆鬥和瘋狂虐殺。清華附中,我班裡四面的牆上貼滿了謾罵的大字報,都是針對我的。
我已不敢待在學校,每日在家躲著。一天,兩個同班女紅衛兵突然雄赳赳來抄家,把所有地方翻了個遍,但凡有點兒蛛絲馬跡我們可能都會沒命。母親嚇壞了,廚房的下水道里是她剛剛扔掉的金項鍊,後院泥土底下是前一天匆匆埋起來的砸爛的黑膠唱片,和她剪碎的旗袍。這倆同學在屋裡屋外翻騰檢查著,只要稍稍注意一下院子裡土壤的顏色,就會發現灰白的干土面兒中有一塊地方顏色發深,但她們沒有發現,悻悻地走了。
父親已被下放到內蒙監視勞動,做英語老師的母親則被學校開除,在街道上掃大街掃廁所。全家都是政治賤民,生命沒有任何意義,不屬於這個世界。每天,牆上的像微笑地看著我們,讓我覺得更加卑賤與孱弱。我們住的那幢樓,鄰居全是部隊幹部家庭,只有後搬來的我們是另類,低頭進出,不敢與任何人打招呼。母親善畫畫,想找個地方去做美術臨時工,掙些錢緩解一下家中困境,居委會王主任皮笑肉不笑地對她說:「老錢,只要我活著一天,你就別想出去工作。呵呵!」
樓下黑洞洞的樓道門就像撒旦的大口,那是我們全家停放自行車的地方。突然一日自行車車帶全都被扎,然後就是連續被扎,最多的一次,一條新帶被扎了三十多個窟窿。記得補帶的師傅鄙夷地上下打量著我:「你這是被人扎的,你什麼出身?」那個眼神深深刺進心臟,刺出眼淚。
所以後來不管多累,每天我們兄妹三人都吭哧吭哧把幾輛自行車統統搬到三樓,推進屋裡。出入樓道的時候則低頭快走,不敢和任何鄰居眼睛對視。
記得是個深秋的日子,萬物肅殺,樹葉凋零。突然一聲巨響,家中的一塊玻璃窗爆碎,幾個硬物破窗而入,裹攜著碎玻璃嘩啦啦差點兒擊中我們的身體!全家驚呼起來,仔細看,硬物是幾塊磚頭,顯然是有人故意扔投的。
我跑到窗框邊側目張望,樓下已經沒有了人影。
我們苦苦猜測,是誰幹的?怎麼辦?還能怎麼辦?千萬別和他們講理,趕緊找一張沒有主席像的報紙,把窗戶糊起來。
沒想到過了幾天,襲擊又一次發生,然後就成了常態!不知何時,不管是在吃飯還是睡覺,突然就是一聲巨響和滿屋橫飛的「子彈」,然後就是我們撕心裂肺的驚恐大叫。怎麼繼續生活?巨大的恐懼裹挾著我們,出門時鄰居們鄙視的目光像是在殺人:「你們他媽還活著幹嘛!」回家後窗戶如獠牙之鬼,隨時都要撲上來把我們撕碎。
父親在內蒙每日交代歷史問題,怎麼也過不了關。掃大街的母親勞累疲憊,回到家中卻無法入睡,精神瀕臨崩潰,還要打起精神安撫驚恐的我們。玻璃窗已經破碎不堪,隨著狂風猙獰地咆哮。又一次襲擊之後,僅剩下的一塊碎玻璃嘩啦啦落了地,我氣得心動過速,血脈噴張,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
管它什麼出身,什麼崽子,和他們拼命去!三竄兩竄跳到樓下,眼睛充滿血絲,像潑婦一樣插著腰,學著用此生聽到過的最粗俗語言,對著全樓那些深不可測的窗戶破口大罵!那些廁所牆上看到的下流話從嗓子裡連珠炮般噴發出來:「××××××!別以為你們狂,我TM也有人!我知道你們是誰,住哪兒!聽見了嗎?你們等著!再敢扔一次磚頭我就叫來人,看誰還能活著出來!不信你們就試試!××××××!」罵得驚心動魄,穿雲破天!罵畢,仍舊咬緊牙關睜圓眼睛豹立在那兒,怒視黑乎乎窗戶後面的人影,等著磚頭的疾風暴雨向我襲來,然後壯烈躺倒。奇怪,怎麼沒人出來應戰?怎麼是死一般的寂靜?
鬧了半天,他們也吃軟怕硬!我從此知道了謊言的巨大威懾力。只要不要臉,敢說謊,別管多難聽多下流,罵出來就是真理,就有人信!
從此,我家的窗戶再沒被人砸過!
四
當時的清華附中,校長老師被數次批鬥慘打,剃了陰陽頭。紅衛兵在學校大門旁用樹枝搭了一個低矮的狗洞,橫眉豎目呵斥著校長老師們從狗洞裡鑽進鑽出。每個班都揪出反動學生或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黑苗,我們班長曉芬的家庭出身是工人,根紅苗正的紅。但她學習成績優秀當了班長,因此由紅變了黑。
在一次對曉芬的班級批鬥會上,一個不是紅色出身的女生出於表現自己的迫切需要,忽然憤怒地站了起來,堅定地走向曉芬,直盯盯看著她低垂著的面龐,同學們都開始興奮,以為會有一個革命的舉動出現,比如扇一個大嘴巴子,或者乾脆幾個,然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高舉手臂喊一句口號。沒想到的是,一口濃濃的東西黏糊糊地從她嘴裡噴射出來,準確地落到了曉芬楚楚可人的面頰和柔軟的頭髮上。
大家都差點兒吐了。
後來,我和曉芬,兩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崽子惺惺相惜,成了好友。
再後來,那場動亂結束了,父親平反了。飛越駝峰的事跡被人寫成報導文學和小說,兩航起義被拍成電視劇。父親和他的中航央航同事們,被人稱為抗日英雄,中華脊樑。
如今想到這段經歷,常常時空錯亂,覺得歷史和現實交錯出現,混亂不堪。黑白還會顛倒嗎?戰爭又快來了?敵人又蠢蠢欲動了?懵懂無知的孩子們還會想著上戰場獻身,做英雄的炮灰嗎?那個修改了我們基因的魔鬼,還在血管里爬行嗎?
如今的我,已經鬢白。本以為這一頁早就翻過,沒想到它那麼強烈那麼執著地從心底向上冒,讓手指不能停歇,敲擊鍵盤聲音的後面還蘊含著什麼酸楚和感悟,只有親歷者心中明白。
如今的我,經常沉浸在回憶中不能自拔。想起父親說的話:「如果不是那個美國飛行員替我值班,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我,也就沒有你了。」我經常深深地自責,父親在世時,我怎麼就沒有想起來問一下那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他還在喜馬拉雅的冰川中熟睡嗎?他們飛機的殘骸還在駝峰山谷中閃閃發光,給後來的飛機當做航標嗎?他叫什麼?有什麼辦法能找到他的名字?
我想,每個清明節都在想,想為他送上一束最大的絕美鮮花,讓無盡的芬芳與感恩擁抱覆蓋著他,然後,在他的墓前長跪不起……
終於在作家劉小童所著《駝峰航線》一書中的最後幾頁,看到了這樣的幾行字描述當年父輩的飛行:「邱吉爾先生說『在人類戰爭史上,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那麼多的人的生存,要依賴那麼少的人。』在戰爭年代,中航、印中聯隊,就是這些人和他們那些破爛飛機,使四萬萬中國人民,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堅持到了最後!」
在這本書中的附錄一和二,我終於找到了朝思暮想的犧牲者的名字,先是53位中國名字,然後就是英文名字!我向後翻著,不是幾十人,不是上百人,一共9頁多密密麻麻的生命,我含淚數著,落淚數著,一共1508位英雄!
七十年時光薄如蟬翼,那些鮮活帥氣的年輕生命,穿越時空,倏忽撲面而至。
這些靜穆的偉大名字默默地告訴我:他們是我的父親,我們大家的父親。
不能再顛倒黑白了!他們是勇氣,是責任,是擔當,是我們向和平不懈努力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