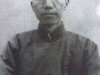宋彬彬走了,很多人說紅衛兵時代過去了,我不認同。
有大咖說,紅衛兵對中國的危害有兩次,一次是他們響應號召造反,二次是他們成年後成為社會中堅。而且,二次危害甚過第一次。
宋彬彬只是機緣巧合成為紅衛兵時代的一個符號,她不是紅衛兵運動的推動者,也不是紅衛兵思潮的肇始人,她既不代表紅衛兵時代的開始,也不意味紅衛兵時代的結束,而且二次紅衛兵的時代沒她什麼事!她早就離開了中國。
宋彬彬成為紅衛兵符號l是因為她上城樓給偉大領袖送臂章和被領袖改名宋要武。
送臂章有幾個版本,大體經過是,她作為紅衛兵代表參加了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她離主席台很近,因而突生一個想法,給主席送臂章。負責保衛工作的謝富治和她的父親宋任窮很熟悉,就同意了,她就走上前去,於是留下了歷史的經典一幕。
臂章是她自己的,最原始照片顯示,是紅布黑字,而不是後來修飾過的彩色照片的黃字。
第二個名細節是,主席給她"改名",大致經過是偉大領袖問她叫什麼名字,答:宋彬彬。領袖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領袖說:"要武嘛"。
雖然宋彬彬否認她曾改名"要武",但當年的《光明日報》上白紙黑字寫著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為主席戴上臂章》。

她紅衛兵代表的形象就此定格。宋彬彬後來說,當時的她根本寫不出那樣的文章,文章就是就是記者代筆和杜撰。第二天《人民日報》轉載了那篇文章,這是當時最權威的兩張報紙,"兩報一刊"的兩報。
雖然宋彬彬一直解釋,當時偉大領袖只是隨口一說"要武嘛",她也從來沒有改名叫過宋要武,但是,經過媒體宣傳,宋要武成了她背負一生的符號。
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是8月18日,之前的8月5號,北師大附中黨委書記卞仲耘死於紅衛兵之手。宋彬彬就是北師大附中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
她說她沒動手,但至今沒有清查是誰動的手,於是鍋就由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她來背。當然,這個背也只是輿論上的,她沒有受到任何司法的追究。
事實上,她只是機緣巧合,出現在一個萬眾矚目的場合,而成為紅衛兵的符號,論影響,論危害,比起她,應該對紅衛兵運動承擔責任的,大有人在,清華附、人大附、四中,那些紅衛兵組織創建的最早倡議者、發起者,他們更是時代悲劇的助推者。
有位作家自稱就是紅衛兵名稱的起名者,這些原始推手更應該承擔歷史責任。
紅衛兵打人、殺人、抄家焚毀文物,對中國破壞很大,但有人說,未來這些人掌權後對國家危害更大。這種影響不僅在於人,更在於一種思想影響。
宋彬彬1980年離開中國,去了美國,改名宋岩,還入了美國籍。但是,美國人宋岩一生都擺脫不了宋要武這個名字。
2003年,56歲的宋彬彬回國創辦公司。她回到中學,對紅衛兵的作為做了道歉,但並沒得到老師的原諒,她也曾在多個場合對卞仲耘之死她的責任做澄清,也沒得到卞仲耘丈夫原諒。
她的名字宋岩學校校慶時被寫進校友名人錄,還受到校內外輿論質疑,她終身都擺不脫"宋要武"三個字。
宋彬彬的文革責任,自有當事者評說。但是我覺得,給紅衛兵代言,她肯定當不起。她的死也說不上是紅衛兵一代的終結。
紅衛兵運動作為一種思潮,一種精神氣質,一種價值觀念,一種行為方式,會很長時間存在,因為紅衛兵影響的不只是那一代人,至少包括沒有經歷文革三年的七十年代的紅小兵。
宋彬彬走了,紅衛兵時代沒有終結,紅衛兵一代還在,紅衛兵的弟弟妹妹紅小兵也在,終結他們的影響可能還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