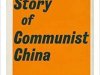蘇維埃即代表會議,是蘇俄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時期設立的一種政治制度。一九二七年廣州起義時中共就建立了短短數天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八年毛澤東在井岡山地區建立了正式蘇維埃地方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蘇俄國慶日)共產黨人在江西、福建交界處的瑞金縣葉坪村召開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到會的有中央區,閩西區、湘贛區、湘鄂贛區、贛東北區、湘鄂西區、瓊崖區及上海、武漢的工人代表共一百九十人,鄂豫皖蘇區因戰時交通不便未參加這次會議。這次大會宣布成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下設勞動、土地、財政、軍事、外交、內務、教育、工農檢查部等部。中共正式宣布中國已經分裂為蘇維埃的中國和國民黨的中國,公開主張武裝推翻國民政府,並在蘇區進行了長達五年的專制統治,給中國特別是所謂蘇區帶來了深重災難。幾十年來由於中共的片面宣傳,人們對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真相知之甚少。今天我們從不同角度反思歷史,戳穿數十年的欺騙性宣教,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偽「憲法大綱」
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偽「憲法大綱」開宗明義地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是「有系統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僧侶……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在這個政權的武裝力量上規定「惟手執武器參加階級鬥爭的權利,只能屬於工農勞苦大眾」。在「公民」選舉權上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比例名額。一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它的民族政策是「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區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規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宣傳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則宣稱「中國蘇維埃政權宣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客觀存在的鞏固聯盟」。
這個偽「憲法大綱」是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天壇憲法》基礎上的嚴重倒退。由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貫穿著民主精神,規定「中華民國為永遠之民主國」,設立有上下兩院的國會並充分保障人權。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凱頒布的《天壇憲法》也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並保障國民的言論、出版、結社、請願、營業和遷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為一黨獨裁、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也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的是回歸憲政,而實際上國民政府也於一九三六年公布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可見不管是孫中山時代、還是袁世凱、蔣介石時代,追求民主始終是時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們打著民主的旗幟,心懷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們也不敢公然主張實行階級專政。即使前進的道路曲折迂迴,中國社會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艱難跋涉,沒有一個政治集團公然宣稱進行專政統治。
偽「憲法大綱」在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規定一個可以階級凌駕於其它階級之上,規定只有他才能手執利刃實行階級專政並剝奪其它社會階層的一切政治權利;在「選舉」權上第一次給一個階級以特別的權利,肆意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理;它剝奪所有人的自由經營權利,排斥、拒絕一切宗教,公然踐踏公認的基本人權;它的所謂民族政策無疑為國家分裂打開了綠燈;它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一紙投靠赤俄的賣身契,是自甘做赤俄兒皇帝的政治宣言。這個偽「憲法大綱」與《臨時約法》、《天壇憲法》比較,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權利上都出現嚴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張建立一個恐怖的獨裁專制政權,從世界政治史和中國政治史上衡量,都稱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惡法。
二、赤俄領導的中共「革命」及賣國行徑
中共是在赤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一九二零年俄共遠東局派維經斯基來華,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共「一大」綱領提出了「聯合共產國際」,「二大」提出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完全交出了革命領導權。共產國際不僅直接向中共下達行動指令,而且干預、參與了中共黨內的反陳獨秀、李立山、羅章龍的路線鬥爭。共產國際為中共培訓幹部、提供經費,派出以德國人李德為首的軍事顧問指揮作戰。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塞的過問下,王明被安排進中央委員會,後又擠進了中央政治局。中共在以赤俄為首的共產國際領導下,以推翻國民政府為目標,成為中國政局的動亂源。實際上,中共不但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成了赤俄的「兒皇帝」,它唯蘇俄馬首是瞻,幾乎一切政令都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準。
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僅供黨內傳閱的《王明言論輯》記載: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中國問題委員會上,史達林就對中國同志說:「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便不會有革命的勝利」。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的宣傳大綱》中要中共注意革命過程中的困難,逃陣和變節。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所謂《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黨應準備應付新的廣大的革命浪濤的高漲;黨對這新高漲的革命浪濤必須的任務,便是組織,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因革命的任務,只有用武裝暴動和推翻現存政權的方法才能解決」,慫恿中共舉行武裝暴動,並指責中共「一部份在農民區作指導工作的同志,迷戀著零碎的必遭失敗的游擊戰爭,而不注意把運動準備擴大到廣大的範圍」。指示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決的反對一切在城市和鄉村中沒有準備的暴動」,「黨應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務,在準備城市與鄉村或鄰近各省共同聯絡出動,並在一廣大範圍中組織與準備這各動作(暴動)。因此,便須與過去重視散漫不相聯絡的必致失敗之游擊鬥爭的傾向奮鬥(這種危險已見於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對中共引狼入室,賣國求榮的指責並不是沒有根據。
在武裝暴動上,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在現在當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必要在農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組織,重新創造自己之政治影響的基礎,在動員農村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貧民……採取堅決的勇敢的鬥爭」(一九二九年《紅旗》第六十期)。指示中共組織僱農工會和貧農團。在蘇維埃區域實行軍事紀律。要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然後爭取全國的勝利。
在蘇維埃政權建設上,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指出:必須在最有保障的區域裡建立起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夠為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工鞏固的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國際指示中共「黨團必須是蘇維埃的提案與決議的創首者及召集報告會與其他各種會議的發起人。」
關於土地問題共產國際幾次指示「蘇維埃區域之中,黨的注意的中心,應當是土地問題的解決……同時,黨要宣傳國有土地的中心口號」。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給中共發出《關於農民問題的信》指導對於富農的工作。
在經濟方面,國際指出在蘇維埃區域要有一定的經濟政策。「實行向富農及一切剝削者徵發,限制或調節一部份為境內廣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軍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烯料、鹽、煤油等)底價格。」有些地方限制一切商業自由,限制一切物價,甚至實行強迫挨戶徵發。
關於國統區的鬥爭,國際決議:「黨應當聯繫政治的經濟的鬥爭,儘量去發展政治罷工,定出準備各地的或者幾個主要工業城市的同盟罷工方針。組織政治罷工的時候,除反對軍閥和國民黨的口號之我,必須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眾生活的……經濟要求,……同時,應當儘量去鞏固赤色工會,堅強工人自衛的團體」。國際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里農民運動的策略是:應當是發動和領導抗捐、抗稅、抗債……等各式的鬥爭引導農民群眾走向游擊戰爭和地方起義。
關於民族問題,以蘇俄為首的國際再三指出:「中國境內有千百萬回民,還有千百萬的藏、蒙、苗、瑤、滿以及安南、朝鮮等等少數民族,對這些民族的工作與反帝運動及土地革命有極大意義和作用」。企圖挑起民族矛盾,從中漁利。
在黨的建設上,國際指出:首先就要使黨數量發展,黨報和數量與質量加多和提高。
由些可見,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完全沒有所謂革命的自主權,它的一切行動都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命令和精神,中共在實質已成為赤俄顛覆中國政府的工具。對此,中共並不諱言。它公開地說「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實行在國際直接領導之下,號召各級黨部完全遵照國際決議及指示執行實際工作。中國共產黨的一切黨員……像一個人一樣,一致起來實行共產國際的路線(《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我們黨在中央領導之下,不怕這一切困難和複雜性,堅定不移地執行自己的總政治路線——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的路線」。中共四中全會更是提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這個口號,是使黨更加布爾塞維克化和蘇維埃革命更加勝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證」(《共產國際》中文第一期第五卷)。中共領導人在分析中國革命的優越條件時興致勃勃地說:「中國共產黨有以史達林為領導的列寧主義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王明《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連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後來的清剿中土崩瓦解,不得不倉皇逃竄前,也需向共產國際請示,共產國際復電同意後才狼狽出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東北中東路理事長兼全路鐵路總辦呂榮寰根據國民政府的指令,以武力接收中俄共管的中東鐵路。八月,中蘇邊境戰爭爆發。蔣介石政府以「一致對外」號召全國人民與蘇聯抗爭。而此時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通過的《反帝國主義大戰的鬥爭與共產黨員的任務》向中共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這一戰爭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國的政府一敗塗地,而且要積極的努力保障蘇聯的勝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批示精神,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與「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且隨著事跡發展的過程而轉變成實際行動」(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在這場中蘇邊境戰爭中,中共公然叫囂要用「實際行動」站在蘇俄一邊,攻打中國,同時污衊中蘇邊境戰爭中維護了國家利益的國民黨是無恥的合盤的出賣民族利益。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國的一致反對,馮玉祥、閻錫山、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都發出聲討赤俄肅清共產黨的宣言通電,主張一致對外。就連一些正直的共產黨人也對這種赤裸裸的賣國行徑表示不滿,七月二十八日,陳獨秀寫信給中央,批評中央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政策。他認為這次邊境戰爭是國與國間的糾紛,國際間的糾紛。而中共執意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間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武裝干涉蘇聯的一部份,因而中共必須站在蘇聯一邊,不惜用「實際行動」來對抗自己的祖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團結一致,抵抗外侮是社會各界的共同心聲。當此關頭,中共仍然把反國民黨和反日本帝國主義並列,甚至認為前者更重要,他們污衊「國民黨政府事前參預了日本武裝占領滿洲的計劃」。甚至說「推翻國民黨政府,是勝利地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中共的擾亂是「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不能痛下決心反擊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在蘇聯的策謀下獨立,但一直沒有得到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政府的承認,對此赤俄極為不滿。中共秉承蘇俄的意旨,恬不知恥地叫囂「最無恥地,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還不承認外蒙古是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而把外蒙古看成中華民國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他們煽動民族矛盾,污衊國民政府「對於蒙、藏、回、瑤、苗、黎、僮等弱小民族,施行其殘忍的屠殺和壓迫,對於高麗、安南、台灣、印度、菲律賓等的革命戰士,經常地把他們逮捕起來押送給英、日、法、美帝國主義劊子手處死」。聯繫到蔣介石一路北伐,致力國家統一和偽「蘇維埃憲法大綱」中鼓吹蒙、藏、回、瑤獨立的條款,誰愛國,誰賣國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三、紅軍的基本構成及實際狀況
關於紅軍的基本構成,毛澤東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說:「紅軍的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然而他又說:「紅軍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軍隊來的」。王明在《武裝暴動》的序言指示:「在許多地方的土匪漸與農民運動相接近,漸漸直接的幫助農民的鬥爭,這種事實尤其使共產黨員不能不注意到他們對於土匪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應當鑽進土匪隊伍中去……可以組織他們作革命的爭鬥」;紅軍、蘇維埃政府還和全國的哥老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蘇維埃政府曾發出通知要求參加哥老會的區鄉兩級黨員務必參加開山堂,宣稱「有蘇維埃,有紅軍,哥老會就有了靠山」,並鼓勵蘇區內的大爺、當家、管事的要積極到白區發展(周恩來《關於哥老會問題》),可見紅軍的構成從一開始就摻雜著土匪、山堂、幫會成份,帶入了吸大煙、充光棍等惡劣習氣。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承認:「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他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還承認「湘贛邊界寧岡各縣的農民只願在本縣赤衛隊當兵,不願入紅軍,因此紅軍簡直尋不出幾個湘贛邊界的農民」。為了保證有充足的兵源,蘇維埃政府動用種種手段開展了一系列「擴紅」運動,使紅軍規模迅速擴張。
擴大紅軍的方式一是鼓動。毛澤東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東西群眾鬥爭熱忱最高漲時,要適時地提出擴大紅軍」。就是在這樣的場合興國縣大地鄉曾一次動員了十三個人當紅軍。對於經過屢次動員而無動於衷的農民則組織「兒童團,恥笑隊,宣傳三四次不去便恥笑他」(《長岡鄉調查》)。二是利誘。一九二八年湘贛邊區《土地法》中規定:「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僱人代替耕種」。僱人代種的標準是:農忙時每家幫二十五個工,平時平均每家幫十個工。紅屬幫助紅屬,每天需付一毛半,紅屬幫助群眾,每天能得兩毛,群眾幫助紅屬則不付錢。而遍布蘇區各鄉的油鹹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紅屬才給賒帳。貨缺時,紅屬先賣,減價百分之五,社員後賣,不減價,非社員再後賣。其糧食調濟局,賣出時先賣紅屬,再賣給困難群眾。賣給群眾要扣除損耗。紅屬無錢可以借糧,秋後歸還,不取利息。無疑,這樣的優惠條件在極端貧窮落後的農村地區對廣大農民有著極大的誘惑力。三是徵兵。蘇維埃《憲法大綱》就規定了「實行徵兵制度」,蘇區的徵兵就是通過強行攤派兵額,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澤東《長岡鄉調查》關於擴大紅軍一節中就有生動記載:在「擴紅」會議上,「長岡村代表答應擴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應四人,新溪村代表答應三人,泗網村代表答應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這至少說明有一部份農民參加紅軍並非是出於自願。四是收編俘虜。通過宣傳鼓動、利誘和脅迫,一些農村甚至出現了男子都當兵吃糧的局面,如興國縣長岡鄉十六至四十五歲壯年七百三十三人,當紅軍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鄉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歲男人五百五十五人,當紅軍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歲七百六十五人,當紅軍四百四十二人。未參加紅軍的在鄉男子也編入赤衛隊、兒童團,如長岡鄉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歲男子編赤衛軍一排,全鄉六十六人,除重病殘廢二十人外,全部編入。同齡女子編赤衛軍一連,全鄉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殘二十六人外,一律編入。十六至二十三歲青年編少隊一大隊,男女合編,全鄉一百零一人,除病殘十五人外,一律編入。通過上述四種方式,紅軍規模迅速膨脹,中央蘇區的紅軍兵員最多時曾達到八萬多人。
這種迅速擴張起來的軍隊,素質低下,良莠不一,因而軍隊作風極為惡劣,下級士兵境況十分悲慘。主要表現為官兵等級森嚴,打罵士兵、虐待傷員,士兵逃跑不斷,甚至還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殺現象發生。毛澤東在《廢止肉刑問題》一文中披露:「各部隊中凡打人最厲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顯著的例子,如三縱隊第八支隊部某官長愛打人,結果不僅傳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軍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隊第二十五大隊曾經有一時期來了一個最喜打人的大隊長,群眾送給他的名字叫做鐵匠,結果士兵感覺沒有出路,充滿了怨恨空氣。特務支隊第三大隊打人的結果,跑了四個伙夫,一個特務長,兩個鬥爭好久的班長,其中一個名蕭文成,臨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壓迫才逃跑。四縱隊初成立時,一、二、三縱隊調去的官長,一味地蠻打士兵,結果士兵紛紛逃跑。二縱隊逃兵比任何縱隊多,原因雖不止一個,然二縱隊下級官長的大多數打人的習慣最厲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縱隊曾發現過三次自殺事件(排長一士兵二),現在紅軍中一般士兵的呼聲是『官長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澤東在另一篇《優待傷病兵問題》中披露:「官長替傷病兵送茶水、蓋被窩、隨時慰問等習慣,在紅軍中簡直沒有。官長對傷病兵,采一種不理問態度,甚至表示討嫌他們的態度」。「行軍時官長以至士兵對在沿途落伍的傷兵完全不表示一點同情,不但不為他們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罵,或無情地驅逐他們」。「傷兵傷後,七八天還沒有衣服換,調養費病官有,病兵沒有」。「飲食惡劣」。「與當地群眾關係不良,以致傷病兵看醫院如牢獄,不願留在後方」。「使士兵不滿意紅軍」。這樣的體罰虐待,使下級兵士不無法忍受,紛紛出逃。如長岡鄉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鄉蘇維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蘇維埃幹部、紅屬婦女和兒童團組成為宣傳隊、突擊隊,在各鄉開展逃兵歸隊活動。
四、蘇區的土地革命
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土地狀況據當時國民政府調查是:全國百分七十三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十五畝土地,百分之五的家庭戶均擁有五十畝以上的土地。資本主義式的僱工租地大規模商業化農業經濟並不普遍。百分之三十的佃農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佃農耕作自己的土地同時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為百分之四十三。除地租較高外,土地兼併不是非常嚴重,絕大多數農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為保障僱農利益,國民政府一九三零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給予佃農無限期續約權,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國民政府還制定了將租金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七的政策。佃農並不一定非常貧窮,有的佃農大戶反而比小自耕農富有。因此整個二十世紀統治中國的意識形態「耕者有其田」可以說是人們對現代經濟學無知而接受的一些政黨的機會主義口號。由於這類口號給國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財產,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權力,它為以後導致經濟災難、政治動亂的政治遊戲規則的盛行開了一個惡例(楊小凱《民國經濟史》)。
然而蘇維埃政權並未顧及當時農村的土地狀況,而是全盤照搬馬克思主義關於實行土地「國有化」的理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把剝奪地產作為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的必要手段,蘇維埃政權的土地革命完全貫徹了這一理論和充分運用了這一手段。
毛澤東一九二八年制定的湘贛邊區《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竹木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後,除老幼疾病沒有耕種能力及服公眾勤務者以外,其餘的人必須強制勞動。這部蘇區最早的《土地法》不但沒收地主、富農、中農土地,而且還沒收貧僱農、佃農擁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廟、宗祠、義莊、學田等公共土地,並勒令一切有勞動能力者強制勞動。「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潮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說明那裡的土地革命遭到各個社會階層的普遍反對。一九三四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對此作了修改,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分配」。同時,沒收地主財產,沒收富農土地及多餘的耕牛、家具、房屋。「只分了些壞田、破屋給他們,現富農耕牛、農具需向人租」。經過土地革命以後,連毛澤東也承認「現在富農家況比僱農差」(《長岡鄉調查》)。這樣的土地革命無疑徹底解決了土地兼併問題,但由於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國有」政策,農民並沒有成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們徹底喪失了自己對於土地的完全權利,全部成了另一個僱主——蘇維埃政府——的佃戶。
即使是這樣的土地革命也被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層視為革命不徹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人或者只請過一二年長工的富裕中農也放在富農一類,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如勝利縣原劃地主富農二千一百多家,後地方蘇維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為中農或貧農,錯劃者占一半以上。而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一號訓令:「在暴動後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有錯不糾,公然掠奪中農、貧農財產在蘇區暢行無阻。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員會發出第二號訓令,要求蘇區重新分田,「限二月內必須徹底分好,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當時僅中央蘇區約有三百萬人口,地主、富農以占百分之五計,至少有六萬人完全失去了生活來源。同年六月,蘇區開展了一次查田運動。毛澤東甚至說:「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通過階級就是決定階級成份,是對這個人決定生死的時候」(《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通過查田運動,一些剛分到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採取了株連手段,如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斗」(《長岡鄉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