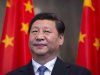摘要:「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
緣起
先說一句白樺的《苦戀》(改編拍成電影後,叫《太陽和人》)。劇終時,雪停天晴,劇中主角凌晨光已走到生命盡頭,他拼著最後一點力氣,在雪地里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這個問號所要表達的就是他女兒星星問他的那句話:「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
這在那個時代,一如當年的屈原,只能是一句「天問」。什麼是天問,就是人在無奈絕望之極,痛苦地叩問蒼天:蒼天啊!請你告訴我吧,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當然,蒼天不會開口,因此只能是無解。
由眼下情形來看,已經八十五歲高齡的白樺先生要想在生前在生他養他的中國大陸看到公開放映這部給他帶來嚴重爭議的影片,確實有點懸。大半個世紀,在中國大陸:文藝不是文藝。文藝只是政治工具,甚至就是「傳聲筒」。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很多有思想的中國人,早先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先賢,後有李慎之、王學泰、鄧正來等一撥中國當代學者,都發出過類似疑問:為什麼在中國個人沒有地位?沒有獨立、自由、自尊?甚至就連在某些方面受到廣大網友詬病的中國著名自然科學家錢學森,晚年也發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創新人才?」
為什麼?說到底,就緣於統治者總是向你灌輸:國是家!沒有國,就沒有家!正如近一百年前當時很快就要成為中共第一任領導人的陳獨秀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一文開篇所講:「愛國!愛國!這種聲浪,近年以來幾乎吹滿了我們中國的各種社會。就是腐敗官僚蠻橫軍人,口頭上也常常掛著愛國的字樣,······似乎『愛國』這兩個字,竟是天經地義,不容討論的了。」這兩行引文放到今天,有誰敢說不合適嗎?
若不信,前段時間,只要你空閒時觀看大陸電視節目,就一定能天天見到一個又一個央視頻道在正式節目間隙插播這樣一條「愛國」廣告:一個採用「動」而不「漫」的形式製作的假人「小女孩」,穿著火紅的小棉襖,先是蹲在地上,偏頭佯裝思考,一會兒,站起來,蹦蹦跳跳,開口像道白,第一句就是:「國是家······」(最近發現又換了新詞)
如果不用腦子,感覺很可愛。孩子嘛,百無禁忌。如果連孩子說話也不能自由,那我們這個社會也就更不是人呆的地方,用魯迅的話說,即中國是一幅「不類人間的圖」。自然,本人相信,這麼大的孩子,絕不會懂得什麼叫「國是家」,用老百姓的話說,不過是「順嘴打哇哇」。可在有人看來不然,他們就是「要從娃娃抓起」,此乃正是好灌輸好洗腦的年齡。《烏托邦》作者莫爾早在五百年前就在他的這篇著作中講了這個「道理」:「······因為在兒童時代所灌輸的思想,會在幼兒的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長大以後,這種思想會伴其一生」(新疆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88頁)。
國是誰的「家」
可難道我們不想培養現代公民?不然,到今天這個時代,為什麼還在毒害孩子純潔的心靈?製作這種所謂「愛國公益廣告」者,實在就是一種「公害」,是一種逆人類社會進步的公害,是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更是一種狹隘的「國家至上」,而這種國家主義,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被當時還是在野黨甚至被國民黨稱作「土匪」的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也就是說當年的中共是堅決反對國家至上反對國家主義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4卷《「好政府主義」》一文後面對「國家主義」有個注釋:「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它抹殺國家階級本質,以『國家至上』的口號欺騙人民服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宣傳『民族優越論』,鼓吹擴張主義。中國的國家主義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後改為『中國青年黨』,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動。」
可誰能想到,近一百年後的今天,原來特別反對「國家至上」的這個黨一旦成為執政黨後,竟也宣揚起「國家至上」來了,並且非但在城市街道的牆壁上毫無顧忌地宣揚「國是家」,且利用電視節目強行向中國大眾灌輸這種觀念,簡直就是在搞「立體轟炸」。不僅如此,就連清明節這種民間祭祀的日子也不放過:今年清明節期間,央視播出一篇又一篇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家書,其中都有「國是家」、「沒有國即沒有家」這種意思,仿佛要將自己當年反對的東西強加給現在的中國人,真是「煞費苦心」。
這一點,就連海峽對岸的同胞都看出來了,台灣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陳宜中博士在採訪知名學者、原炎黃春秋雜誌主編吳思時就這麼說道:「(大陸)當局始終拒絕憲政民主化的變革,反而往國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方向前進了好幾步。」
我不知道我們的執政黨今天給中國人灌輸這種觀念應該被看作是「反」什麼「的活動」,難道也是「反人民的活動」,不然,如何能講得通?最讓人想不明白的是,面對這種「國家至上」的宣傳灌輸,至今在媒體上沒有見到有專家學者公開站出來發表反對的聲音,正是不滿於這一點,本人想就這種話題發表幾句「異見」。
國真的是家嗎?當《南方人物周刊》讓白樺說說由《苦戀》改編的電影中比較滿意的演員時,白樺告訴記者:「許還山的戲份非常少,但演得很動人。我說一場戲。當時秋山被下放農村,請假回來,凌晨光到汽車站去接他,長途車都回來了,沒看見秋山。最後從汽車的夾縫裡走出一個穿著破棉襖,用根草繩捆著腰的人,他就是秋山。擁抱的時候凌晨光說,『你可回家了!』秋山回答了一個字——『家?』(顫抖)僅僅一個字,我的眼淚就出來了。許還山說出了許多意思:家在哪兒?哪兒是家?有過家嗎?」本人相信,白樺的意思,中國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們的「家」在哪兒,或者說哪兒是他們的「家」。他們敢把這個國當「家」嗎?
中國人,自古只知天下,不知國家。到了近代,被列強堅船利炮「打醒」,才明白天下是天下,國家是國家。於是統治者大夢方醒,矯枉過正,竟要人民把國當家。然而國畢竟是國,家畢竟是家。國從來都不是家,家也從來不是國。不然,請問:國有四萬億外匯存底(據說現在只有三萬多億了),國民看病上學為何不免費?不然,在這個「家」里,為什麼有人富得流油,有人窮得要死?有人趾高氣揚,有人卑微低下?有人有幾十套房產,有人連房租都付不起?如此這般,這個國是誰的「家」?是國民的家還是政府的家?是百姓的家還是貪官的家?我敢說沒有幾個未經洗腦的百姓會認為這個「國」就是他們的「家」,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大富起來的大陸人總想逃離自己的祖國,總想逃離他們這個「家」,用吳思的話說:「大陸稍微有點辦法的人,都紛紛往外逃,都想脫離這個國家。」
再提一典型事例,中國如果是中國人的「家」,怎麼可能上街要求公開這個「家」庭某些成員即官員的財產,也會被說成是「尋釁滋事」,反而要被拘留?國如果是家,怎麼會發生一起又一起強拆,怎麼會讓這個「家庭」的成員唐福珍自焚(其他因拆遷而自焚者姑且不說)!可見,就算「國是家」,這是一個怎樣的「家」!
國如果是家,為何要冤殺聶樹斌,冤殺呼格吉勒圖?我估計,他們在被刑訊逼供時、在要被執行死刑時,恨死這個「家」了。特別是那個呼格吉勒圖一案:一個十八歲青年,我不敢說他有多「愛國」,但至少很純潔,有正義感。當他發現一樁命案,與同伴第一時間趕去向公安機關報案。然而,令人痛心和發指的是,在呼格吉勒圖心裡一定是莊嚴公正的國家公安機關卻反而認定他這個十八歲的報案者就是「強姦、殺人犯」,而且僅僅在兩個月後就對其執行了死刑。天下竟有這樣的奇冤!無論是明人馮夢龍、凌濛初的「三言二拍」,還是根據他們的話本精選出的《今古奇觀》,本人都翻閱過,裡面確實講了一些冤情冤案,但再怎麼冤,都沒有冤到呼格吉勒圖這個份上!
對其刑訊逼供的警察的心是什麼做的,為什麼比蛇蠍還要狠毒,比豺狼還要殘忍?他們有兄弟嗎?他們有兒子嗎?當呼格吉勒圖遭受殘酷的刑訊逼供和要判他死刑時,你如果還要跟他說「國是家」,我想,只要他在自由狀態下,一定會向你質問:我要這樣的「家」幹什麼!如果國真是我的家,會如此這般對待我嗎!
我知道,在我們這種國家,進司法機關或是當個警察,不需要特別條件,只要是個人,四肢健全,不呆不傻,就成;如果再有點「關係」,那就更不是問題,哪怕是街痞混混,說不定也能「弄個團長旅長乾乾」。不知是否正因為我們是這樣一種「國情」,才會發生一樁接一樁重大冤案,全國單是被曝光的冤殺案就已不止三兩起了吧,至於沒曝光的,誰也說不清,只有上帝知道。不過,有時想來,再怎麼著,那些「刑事偵查警察」也還是應該長著一個正常人的腦袋吧,公安機關總不至於弄幾個傻屌去偵破案件。既然如此,怎麼就能想到來報案的一個不諳世事的青年就是殺人犯呢!這需要怎樣的「天才」腦袋才能想得出啊!要不,就只能說明,我們有些炎黃子孫的內心太陰暗太齷齪,簡直就已經異化成狼心狗肺了。
可見,國不是家。國如果是家,怎麼會常常讓「家人」感覺到沒有好日子過呢?換而言之,正因為統治者不斷地強調國是家,緊接著這個國就有可能成為「黨國」,而且蔣介石時代如此,毛澤東時代更如此。1978年後感覺略好一點,可近段時間又給大家弄得人心惶惶,仿佛我們又要恢復蔣、毛時代的「黨國」一般。而一個國家一旦成了「黨國」,緊接著一切荒唐也就會順理成章地出現了大陸人面前。
說到這裡,插幾句閒話:本人之所以十分反感乃至厭惡像大陸歌手孫某人演唱什麼旗幟比他的生命還重要,只要看一看此人在公眾場合的表現和油腔滑調的形象以及網上對他的「揭底」就不難明白,此人完全是在忽悠廣大聽眾,即使說得好一點,也不過是靠裝腔作勢混口飯吃。像他這樣一個人,當真有他所唱的那種「旗幟」需要他用生命去捍衛乃至去換時,他肯嗎?如果不肯,憑什麼要向我們這些聽眾灌輸他所唱的那些帶有嚴重意識形態的觀念?按說一個人喜歡演唱什麼是他的自由,別人無權干涉,可這種帶有嚴重意識形態的演唱,簡直就是在給聽眾洗腦,我們不應該聽之任之,並有權利進行質疑。
更惡劣的是,一個國家如果宣揚一種旗幟比一個人的生命還重要,那麼也就很容易發生像文革時期,知識青年金訓華為了在洪水中去搶救電線桿失去他寶貴的生命,而他之所以這麼做,就因為那電線桿是「國家財產」。這還不算完,把國家提到「至高無上」的高度,高於個人高於家庭,並長期宣傳灌輸,且「從娃娃抓起」,結果就出現了賴寧這樣的「救火小英雄」。這位不過是一個小學生的小朋友,救的是山火;為什麼要救山火呢,因為山上的樹木同樣是國家財產,結果失去了他幼小而寶貴的生命。
由於長期灌輸洗腦,在中國人看來,家門外的一切都是國家的、集體的,而只要是國家的集體的,那麼哪怕一塊磚、一塊瓦、一根電線桿、一面所謂「旗幟」,也要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它們在遭到侵害時,自己就應該用生命去保護去捍衛。在國家面前,中國個人不是用一個「渺小」能形容得了的,而是我們每個個人就是一個個螺絲釘,就是一塊磚,甚至就是一個P。既然在國家在集體面前,個人就是一個P,甚至連P都算不上,那麼,一旦某人所謂有資格代表國家代表集體,那麼,這些「螺絲釘」這些「磚」這些P民們也就只有頂禮膜拜,乃至山呼萬歲的份兒了。
「國是家」的惡果
「國是家」的惡果,通過上面「國是誰的『家』」的文字就已有所表述了,下面不過是看一看學者們從學理上是如何來分析認定的,或者說看看「國是家」的惡果到底有多惡。
據吳思講,《炎黃春秋》雜誌老社長杜導正曾說過:「我們知道一點真話可以說,兩點就會傷,三點就會死。」也就是說只能說一點真話,兩點都不敢說,即使如此,用吳思的話說,這已經讓炎黃春秋顯得很突出了。杜導正甚至替炎黃春秋辦刊「總結出七不碰,有七條線不能碰,一碰就可能要命」。你說一個國,如果像家,還會出現如此恐怖的情形嗎?會讓杜導正這樣的老革命也會產生如此恐怖的感覺嗎?
1985年12月下旬,梁漱溟與馮友蘭兩位世紀老人在梁漱溟木樨地的住所晤面,兩人交談時馮的女兒馮宗璞在側,關於馮友蘭諂媚江青一事,馮宗璞本著「童言無忌」的心理替他父親說了一些話。她說:「梁先生來信中的指責,我作為一個後輩,很難過。因為我以為您不應該有這樣的誤會。父親和江青的一切聯繫,都是當時組織安排的······可以責備他太相信毛主席共產黨,卻不能責備他諂媚江青。」又說:「我們習慣於責備某個人,為什麼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後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識分子是改造的對象!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見2015年4月14日共識網:章繼光《八十年代的梁、馮之會》)
這種悲哀的根源,不是別的,正是緣於所有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都被灌輸了「國是家」,而我們要無條件地服從和愛戴這個「家」的「大家長」,甚至要誓死捍衛這個「大家長」。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大腦里不裝別的,裝的只有毛澤東和他的思想。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呢?已經去世兩年多的著名教授鄧正來在他的一篇學術文章中早就痛批過,他告訴國人:國家至上,一定會導致政府獨裁。故而又說道,「只要一個社會是依憑政治結構而規定,只要人們認為政治權力原則上可以滲透或侵吞社會,那麼面對政治強權對社會的侵逼,社會便會缺乏原則性的抵抗和道義或現實的制衡力量。」這是鄧正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說的話,可前有八九年那場風波作證,後有近些年甚至直至眼下中國發生的各種稀奇古怪都仍在證明著。難怪鄧正來在文章中還引用了美國二十世紀政治學家喬治·薩拜因在《政治學》一書中的話說:「對國家加以理想化,以及對市民社會給予道德上的低評價,這兩者結合在一起都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政治上的獨裁主義。」大家看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是不是就是這麼幹的,是否就是這種情形。
鄧正來生前即2007年還有一個著名演講,即《我的學問和人生》,在這篇演講中講了很多中國大小知識分子都不敢講出的真話,即使在發表時很多網站也還了做了「過濾」,比如他說:「90年代以前,我們有一種思維定勢,都是從上往下。國家好個人才好,進一步地,有了明君國家才能好,於是小平、耀邦、紫陽、澤民、錦濤等等,都成為我們企盼的明君。我們恰恰忽略了另一條路徑,一個自下而上的進程,忽略了我們自身的存在、價值、意義和影響。」「什麼是自上而下?就是我們想問題,首先想國家,首先想領袖,我們希望出個明君,他們好,我們就好,都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改革了,我們好,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們的主導性。市民社會本身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我們不僅要從上而下,我們也要從下而上。扭轉整個思維方式,這是個範式。這種範式的轉型非常重要,經濟學也好,社會學也好,歷史學也好,法學也好,這個範式的影響非常大。」
其實,鄧正來的有些意思,已經去世有年的台灣著名的柏楊先生三十多年前在他那《醜陋的中國人》中也講到了:「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廣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5月第2版第5~6頁)這雖是三十多年前的話,卻說到今天無數中國人的心坎里了。
總之,國家主義,國家至上,就是毀滅人性,然後當作實行專制獨裁的藉口。如此之惡的惡果,已經「嘗」夠了的中國人,難道還想繼續「嘗」下去嗎?
2015-5-1成稿,後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