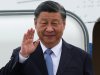滕彪(以下簡稱「滕」):您2016年出版的《完美獨裁》,是您的第一本關於中國的專著,引起學界的熱烈討論。是什麼使您對中國政治感興趣?
斯坦•林根(以下簡稱「林」):首先我對政府、國家以及他們的運作感興趣。中國是最大的、也是最有挑戰性的。你想探討國家運行,就應該了解中國。另外,我已經對韓國和朝鮮做了研究,我認為那裡的國家發展經歷可以成為探究中國故事的相關背景。我曾以為中國和那些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結果卻是,中國的故事完全不同。
滕:然後您就寫作了「完美獨裁」,怎麼想到用這樣一個書名?
林:我發現這個獨裁從它自己的角度來看,是運轉非常有效的。一種完全掌控的獨裁。我用這個書名並非是要讚揚中國體制,而是要提供一個警示:這種獨裁嚴厲,堅固,全面掌控。
滕:您在書中創造了幾個有意思的詞,比如「全控政體」(Controlocarcy),您想強調的是什麼?
林:我的想法是,一方面,這個政權是獨裁的,但有時候它用一種看起來並不獨裁的方式;它痴迷於控制。它並不痴迷於指揮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不像毛時代,人們穿衣、讀書、看戲、娛樂都不能免於被管制。但現在這種體制,仍然是被掌控的。控制是這種獨裁的重要特色,它極其擅長維持控制。因為黨國體制無處不在,它注視一切,知曉一切,對十幾億人實現完美控制。
滕:您書中另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概念是「sophisticated totalitarianism」。在中文裡,sophisticated同時有複雜、精緻、老練之義,我姑且用「老練極權主義」名之。我曾略有闡述:「這種極權,嚴密細緻而不僵化教條,野蠻殘酷而不慌張混亂,表面上光鮮文明、經濟高效、社會安定、民眾擁護,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極具迷惑性。」在您看來,「老練極權主義」和史達林或毛澤東的全能體制有什麼區別?它是一種更有韌性、靈活性和適應性的極權嗎?中國共產黨可以從其他專制崩潰中不斷學習,從而在長時間內避免垮台嗎?
林:這是一種非常堅固、嚴厲的獨裁體制,因此是不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但是他們非常聰明,把這個體制弄得看起來可以接受,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如此。你知道,人們去中國旅行,常常艷羨中國各方面的成就。對內對外,中國當權者都很擅於操控自己的敘事、營造自己的形象。他們也從蘇共垮台學了很多,在北京他們對此做了仔細的研究,他們知道要避免蘇聯的弱點,比如說絕不能失去對話語系統的控制,要一直加固黨和軍隊的聯盟關係,要嚴格維持監控、宣傳和審體檢系,對民間的抗爭絕不能聽之任之,等等。還有絕不能允許黨內分裂,他們吸取了蘇聯解體的教訓,中共將不會以相似的方式解體。
滕: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Kishore Mahbubani有一次講,每年上千萬中國人出國旅行然後自願回國,他用這個例子來讚揚中國模式。你同意嗎?
林:很多中國人旅行,主要因為他們有錢了。他們去歐洲、美國、世界各地,然後回去。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中國人離開自己的國家,或者因為被迫,這一點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或者是因為他們想要孩子到國外受教育,他們把錢轉到國外或者投資、或者為了財產安全。太多的例子表明他們對中國政權的未來失去信心。說中國制度更優越,比民主制度更好,從當政者角度,這是很有說服力的一種話語。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它並非因為提供了發展而更好,而是它的發展以中國人的自由為代價。我們之前了解威權或極權體制,它對部分人有好處,但是它剝奪了每一個人的自由。
滕:另外,很多來自民主國家的人來到中國旅行,並且對中國的發展模式讚不絕口。這種事情在德國歷史上似曾相識······
林:茱莉亞•鮑伊德(Julia Boyd)寫過一本書叫《第三帝國里的遊客:普通人眼中的法西斯興起》,來到納粹德國的外國旅行者,看到的是美麗的村鎮,友好慷慨的人們,並且震驚於德國的進步:鐵道、機場、現代建築,等等。他們對鎮壓、宣傳、審查、個人崇拜以及迫害猶太人的事情並非一無所知,但令人驚詫的是:對這些壓制的了解,基本上沒有影響他們看待這個政權的方式:這個國家卓有成效,成就非凡。今天,到中國的旅遊者情況類似,他們或許知道一些關於壓制人權的情況,但是和他們看到的全部現象相比,只是一個小插曲而已。茱莉亞•鮑伊德(Julia Boyd)的書其實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去極權國家的遊客應該保持警惕性和批評性,很多去了納粹德國的遊客逐漸對他們的天真感到懊悔。今天去中國的遊客應該告誡自己,時刻保持思想的警醒,在這樣的專制政權下,看多東西是你看不到的,而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實的。
滕: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被認為是完美獨裁的一個著名例子,您認為中國現在達到「1984」的程度了嗎?或者,它已經是「1984」的更高版本?我曾用「高科技極權主義」來分析中國當下的極權新趨勢,例子包括大數據、DNA採集、人臉識別、聲紋識別技術、人工智慧、密布的街頭攝影頭、網絡監控、GFW、網格化維穩、社會信用體系、網絡警察、秘密警察等等。我們是否誇大了專制者運用高科技的能力?高科技是否也是雙刃劍,能夠被民間社會和抗爭者所利用?
林:中國確實與奧威爾描述的類似,包括對語言、對歷史、對真相的操控,非常像。但中共更進一步,以一種精緻的方式,利用了奧威爾那個時代無法想像的現代高端科技。人們曾理所當然地認為,沒有獨裁政權可以掌控網際網路;但中國的獨裁者做到了——他們屏蔽信息,以言治罪,還把網際網路作為宣傳機器。還有大數據、人臉識別等等,都被用來實現全面控制,已經達到很高水平。尤其在新疆,那裡已經成為一個從未有先例的警察國家;過去幾年中,那裡的維穩經費每年成倍增長,明目張胆、不擇手段的軍警控制,高科技的電子監控,上百萬人被送到「再教育中心」——「集中營」。在任何國家都沒有見過這樣的控制,但中國實現了。
滕:您知道我曾在中國做了十多年的人權律師,粗略地說,胡錦濤時代,維權運動尚有一定空間,雖然打壓也一直不斷。我們覺得網際網路高科技更有利於民間擴展空間,雖然政府也在利用高科技加強控制。現在看來也許當初過於樂觀了。
林:這方面你知道的比我清楚。過去幾年人權律師群體遭受殘酷打壓。吊銷執照、失蹤、判刑、受酷刑等等,彼此聯合的能力也遭受巨大打擊。對這個勇敢而可敬的團體而言,這是很讓人難過的。
滕:709對人權律師的大掃蕩是中國在1978年恢復律師制度後針對律師群體的最兇狠的一次打壓。
滕:很多人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但忽略了這樣一個現實:中國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種不平等如果影響到中共的合法性?還是說,這種不平等是中共一黨制的某種必需品?
林:在我的書里我考察了中國的貧富鴻溝、貧窮和稅收。我發現中國民眾的稅務負擔非常非常繁重,而政府向民眾提供的服務卻是最少的。不平等的增長非常迅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原因在專制體制。在民主制度下,維持如此高的稅收卻提供如此可憐的服務,是不可能的。社會是要爆炸的,因此中共政權才覺得更有必要維持如此嚴酷的控制。
滕: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共產主義已經日漸式微,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中共官員,只相信權錢二字。這種變化如何影響中共統治?這也是習近平試圖重新恢復中共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的原因吧?
林:我認為,重新啟用的意識形態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強烈的民族主義。習的什麼中國夢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啊,都是民族主義話語。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強大的專制政權,被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chauvinism)所引導。這些是習近平的創新,他使中共愈來愈滑向更嚴酷的獨裁。
滕:您提到了民族主義,您知道,中共建政之前,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義。理論上,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是存在衝突的,但從一開始,中共就自相矛盾地同時利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現在他們覺得更加需要民族主義,您怎麼看?
林:是這樣。這個政權努力營造和控制的話語是,他們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他們需要一個故事,講述統治機器和國家的目標。他們發現這東西不在馬克思的國際主義里而在中國民族主義里。習近平已經公開地、有力地挖掘了民族主義資源。同樣,這也是全控體系的一部分。這個政權自我標榜說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同時,它從未真正信任人民。他們口說民眾擁護,但從未放鬆控制;他們一刻也沒有相信過民眾的擁護是真心實意的。
滕:一些學者和政治家注意到了習近平體制和希特勒第三帝國的相似之處。一黨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意識形態,宣傳,洗腦,民族主義,如此等等。比如新疆正在發生的,就完全是種族歧視、大規模關押和文化滅絕。此外還有個人崇拜和秘密特務系統。在您看來,中國政治滑向法西斯主義的可能性有多大?
林:這個體制有很多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意識形態。鄧小平和他的追隨者做出一種非意識形態的樣子,僅僅是實用主義的、擅長發展經濟的技術官僚。習之後,又回到意識形態,成為一種嚴厲而堅固的獨裁。我稱之為極權,一種訴諸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極權。這是法西斯主義的特徵。我覺得我們不要忘了中國的體制是獨具特色的,它迥異於任何其他東西;但是習的統治之下,它已經具有越來越清晰的法西斯特徵。在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新近出版了《法西斯主義——一個警告》一書,當中有很多有價值的討論,但她似乎迴避了中國。習近平的中國已經走向一種新型法西斯主義。這個政權確實是一個霸凌政權(a bullying state),問問民主人士、維權律師、上訪者、法輪功學員、集中營里的維吾爾人就知道,或者問問中國的外企,或南海的鄰國。但中國仍有底氣和技巧來掩蓋它野蠻和欺凌的一面,它使自己看起來顯得精巧和優雅。
滕:在最近的一封公開信中,您呼籲研究中國的學者不要把當下的中國描述為「威權國家」,而應該正確地稱其為「極權國家」,這在知識界引起了有意思的討論。您認為,學者們不願意把中共政權歸類為「極權」,背後有什麼學術和非學術的原因?
林:我覺得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歸類為極權政權,學術上的理由相當有限。漢娜•阿倫特(Hanna Arendt)對極權做了權威性的、前沿性的研究,極權主義的特徵包括嚴格的一黨制、暴力的統治、統治侵入私人領域、統治通過全面的和非個人化的官僚體系、命令性的意識形態等等。根據這些標準,習近平的中國完全符合極權體制。中共已經無處不在,每個政府部門,每個軍事單位,從中央到地方,每個大學、院系和學生宿舍,每個學校、村落和鄉鄰,每個企業和社會組織。更不用說習近平煽動的赤裸裸的個人崇拜。
最後一根稻草,是中共正在新疆實行的極端恐怖。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被關在在教育中心,被洗腦、被酷刑、被清除民族和宗教特徵、被輸送到外地。這種恐怖還不限於新疆和西藏,很多嚴密的極權手段已經在中國各地實施或者從新疆向各地迅速擴展。比如大數據、DNA採集,以及依據人們的私下言行而確定獎懲的社會信用體系,等等。一部分結果就是社會生活的原子化和社區被摧毀。
很多人認同我的觀點,但也有人反對。不少研究中國的學者要在中國生活,或者要到中國查閱檔案、做實地研究等等,得罪中國的代價太大,我非常理解。另外的原因,我稱之為「中國迷思」(China fascination),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傳統豐富,具有神秘的魔力;一些學者對中國和中國人抱有巨大的期望,因此不願意將其貼上如此貶義的「極權主義」標籤。這是誤入歧途的,但仍是可理解的。相關的,還有人認為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將它和各種令人不齒的邪惡政權歸為一類,就太過簡單粗暴了。
應該補充說明,當我說中國是極權體制時,我指的當然是這個政權,而不是這個國家、文化或民族。
滕:在多大程度上,中國的政治是瑣細的(trivial)?(在林根教授的語境下,瑣細的意思是除了維持自身之外沒有目標的。)哈耶克強調國家本身的「無目的性」(purposelessness),如何理解這種瑣碎和無目標?
林:我認為有一類獨裁是瑣碎的,為了控制而控制,別無其他,沒有使命,沒有理念。但中國的制度不是這樣,至少當下不是這樣。它有使命,有意識形態,有一種目的觀,要讓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央位置。這是非常具有野心的想法。獨裁政權有了目標,不再是瑣碎的,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自我賦予遠大理想的政權。
滕:您的意思是不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更少意識形態,之後習近平有了更大的要讓中國復興的野心?
林:這個野心一直都有。但是要等上一段時間,中國在經濟和其他方面才具有了公開展露野心的實力。現在他們有了這種實力,他們更加努力要使中國稱霸世界。
滕:一些人認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是中共面臨危機——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危機——而做出的集體選擇,您同意這種分析嗎?
林:一直有一類分析認為中共體制處在危機之中。你知道,關於中共將要崩潰的預測有很多,但這並沒有發生。我認為這個制度內部有不少緊張和衝突,而且,習近平犯了第一個錯誤——從他自己的角度這是一個錯誤——那就是,他在今年年初修改憲法廢除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這完全是沒必要的。這完全是展示權力。它向外部世界掀開了幕布,讓外界看到這是一種粗野的專制,最高統治者不費吹灰之力就修改了憲法,也暴露了政權內部的衝突。政權內部當然有衝突,但習近平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他自己的地位。他讓自己成了傲慢的權力膨脹的犧牲品。這是個錯誤,這個錯誤也延申到了系統內部的衝突之中。人們甚至能夠看到,促進經濟增長不夠有力,還有其他因素,都引發了內部的緊張。過去五年裡,習大大地加強了自己的權力,如果不是這個錯誤,他的第一任期的「成就」可以繼續鞏固。雖然如此,我並不認為這個體制有什麼大的危機。黨的控制非常強大,在習近平統治下,在經濟出現困難的預期之下,控制體系繼續得到加強。
滕: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會打擊中共幹部的積極性嗎?極權體制的動力學,比如利益、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國家強力的恐怖,等等,這些因素會枯竭嗎?
林:反腐運動有兩個要達到的結果,一個是讓中國老百姓覺得這個體制更有吸引力。滋生腐敗的環境已經有所改善,所以多數中國人遇到的肆意腐敗現象有所減少,至少看起來如此。另一個結果是,反腐運動已經變成權力控制的有力武器。當所有人都腐敗時,要替換和清除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以反腐的名義來進行。習近平和他的盟友能夠輕而易舉地除掉任何不信任的人,或者任何看起來有威脅的人。這兩方面就是獨裁之下的反腐「成就」。這個體制加給人民痛苦,又把人民從痛苦中解放出來,從而不斷地讓自己得分;中共非常擅長這一套。
滕:一些中國人會對反腐不滿:腐敗是制度性的,但反腐卻是選擇性的,特權家庭沒有受到影響,現任常委包括習近平本人更不可能受到波及。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腐敗是全局性的,植根於體制之中。那麼反腐還會繼續嗎?反腐敗會如何影響習近平的政治計劃?
林:我覺得反腐運動已經完成。日常的腐敗還在繼續,但反腐不再成為中共政權自我展示的一個重大節目;反腐還需繼續,但它不再像過去幾年那樣成為一個核心的政治工具。
滕: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區分了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西蒙斯(A. John Simmons)在理論上區分合法性(legitimacy)與證成性(justification),論述現代政治的合法性只能來自於(通過自由選舉的)承認。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您認為績效——主要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能給中共帶來足夠的政治合法性嗎?
林:在中共領導人自己那裡,僅有績效是不夠的。他們從來沒有相信他們自己是被看作合法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從不放鬆控制的原因。他們歌頌自己說給人民帶來了繁榮富裕,而且說人民對此感恩戴德。但是他們並不真正相信他們真正獲得了政治合法性。
滕: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並毫無懸念地全票當選國家主席之後,國際社會是否在重新思考中國?考慮到中國日漸惡化的人權狀況,不遵守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的規則,甚至境外綁架異議人士和作家(如桂民海、李波、林榮基等案件)等事實,中國的形象是否在變化?進而言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會使中國走向開放社會和民主」,這種廣為接受的看法是否已經被證明是錯的?
林:我認為是這樣。世人很難否認這個事實:中國仍是一個堅固的獨裁體制。在很多方面,這種獨裁對做生意有好處。很多人對中國著迷,只願意去看中國制度好的一面。但是習近平的做法一再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是專制政權。中國絕不是什麼溫和的、友善的民主。我認為,中共政權的所作所為已經讓自己面臨外界的重新評估。
滕:是否有很多中國觀察家開始反思「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將推動中國自由民主」這個理論?
林:這一度是非常有影響的理論,但現在不再有什麼人相信了。長期來看,我們不得而知。短期來看,很顯然,中國的體制沒有朝著一個道德社會前進。過去五六年來,習近平和共產黨在朝更緊固的獨裁方向走。人們曾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開放,但事實正相反。經濟進步加政治壓制,過去覺得不可能,但中國就恰恰就是這樣:經濟現代化了,但政治卻越來越專制。
滕:過去二十幾年,全球出現威權主義回潮,專制國家的影響在擴大,比如俄羅斯、土耳其、菲律賓、波蘭、匈牙利等等,當然還有近70年一直是極權專制的中國。《紐約時報》稱之為冷戰結束後的「威權資本主義回歸」。這種現象背後是什麼?
林:我認為至少有一些獨裁政權是非常聰明的。在俄羅斯,從它自身來看,其威權運作是非常聰明的。中國的新式極權精細、複雜,成熟老練。我同時認為民主國家也存在問題;2007、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之後,在很多方面民主國家的表現相當不好。民主國家沒有真正以惠及大多數民眾的方式進行治理。公正地說,在民主國家,尤其在美國和英國,我們正在看到一種針對不充分治理的反叛。
為什麼專制的影響在加強,需要我們密切關注;對世界來說,這是個可悲的事情。民主國家的確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看到我們處理一些問題上的缺點和不足,歐洲、美國都是如此。
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深化了黑格爾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理論傳統之後——論述說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您如何看?
林:當今政治最強有力的兩個特徵是希臘人發明的,一個是公民(citizen)的觀念,與臣民(subject)相對;另一個是民主。自從人們2500年前發明民主之後,民主的歷史並不怎麼鼓舞人心;我們得到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主幾度瀕臨死亡,在世界把民主遺忘了大約兩千年之後,民主在1787年美國憲法才再次被發明出來,與雅典的公民大會-直接民主不同,這一次是代議民主制。將來民主不能倖存下來,也許是可能的。而且現在,我感覺到,對專制強力的羨慕太多,而對民主憲政的欣賞卻不足。我試圖以微薄之力,促進人們去理解和珍視民主政體和民主生活方式。重複一遍,我認為民主世界需要改善和提高自身。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是,民主並非統治的自然形式,它必須被需要、被創造、被捍衛、被滋養,並且不可避免地暴露於危險之中。
滕:當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政府用「鮭魚政治」來懲罰挪威;在香港,中國政府撕毀「一國兩制」,背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的自由度已經迅速下降,處於危險之中。我個人有一些經歷,比如美國律師協會(ABA)害怕得罪中國而不敢出版我的著作,頂尖大學出於自我審查而取消了我的預定好的演講。作為一個生活在英國的挪威人,您認為中國的這種「出錢封口」(buying silence)政策成功嗎?世界如何來抵抗日益具有挑釁性的中共政權?
林:中國政府出錢封口的做法還是相當有效的。這很令人沮喪,但事實如此。你看到,在我的祖國挪威,為了和中國關係正常化,書面答應了一切條件,挪威政府將不做任何破壞兩國正常關係的事情。這就是保證沉默。在英國,當局處於多種理由希望更多的中國投資,所以也在人權、香港等等問題上不說話。應該怎麼做?我認為應該繼續和中國人民以及中共當局保持接觸和合作。比如學術交流。但是,我們必須用清晰的語言發聲,關於中國政府侵犯人權,關於中國挑戰國際政治秩序。發聲一直都有,但考慮中國日漸嚴酷的中國專制體制,這種發聲遠遠不夠清晰和直截了當。民主國家應該想辦法聯合起來,共同發聲,抵禦中國對人權準則和國際文明的威脅。
滕:在《兩條戰線上的冷戰》一文中,您寫道:「21世紀最初若干年的穩定局勢已經被新冷戰所取代,我們同時面臨中俄兩條戰線。俄羅斯已經走在新帝國主義的路上。中國試圖重歸中央帝國的輝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正扮演越來越活躍和具有進攻性的角色,試圖重塑國際秩序。那麼,中國能走多遠?在發現太晚之前,西方可能放棄對中國的綏靖政策嗎?
林:我很悲觀。我認為中共政權完全能夠掌控他們想要的敘事,以至讓世人廣泛地認為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是正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點是自我審查。我們很多在中國有利益的人,進行大量的自我審查。這利益包括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包括在中國進行研究的機會,等等。民主陣營沒有應對中國極權體制的共同聲音和共同方案,這正是我們急需的。
滕: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在國際事務中的中國共產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國或中國人民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僅僅代表自身——即,一切外交行動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和特權利益?
林:我總是從一個基本假設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其對內和對外政策都是為了永久延續其黨國體制而設計。它的外交政策,還要使中共政權在世界舞台上更有影響甚至獲得霸權。這是否也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我覺得不是,一個專制政權變得日益強大、勢不可擋,這並非中國人民利益之所在。但是關於「中國夢」、「中華復興」的民族主義話語無疑會得到大量中國人的共鳴。中國的獨裁者,和大多數獨裁者一樣,發現民族主義是一張在戰略上有用的牌。
滕:我的問題大概是這些,您還有什麼補充的評論嗎?
林:我知道很多中國觀察者看到了中共政權崩塌的徵兆。經濟表現不夠好,腐敗,高層內鬥,等等。我個人看法是,正確的描述是把這個政權看成是全控政體,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很難看到它會改善。我深深地感到悲觀,中國沒有走向開放社會、在國際上也沒有擔負責任,恰恰相反,它在國家越來越加強控制,在國外則尋求越來越多的操控和支配。
滕:感謝您,林根教授。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英國牛津大學社會政策與干預系教授,出生於挪威。滕彪,前中國政法大學講師、紐約大學訪問學者、人權律師)
出處:《中國戰略分析》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