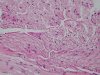想像一下,你的大腦里有著兩個小人,它們在不停地打架,試圖奪取控制你行動的權力。當然,這兩個小人並不是你善意和邪惡的念頭。那它們是什麼?
在很多人看來,這兩者就是我們的意識和無意識:前者是警醒而可控的,後者卻潛伏在意識之下,很難察覺。自弗洛伊德時代開始,就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人類被一種黑暗、不可控的情緒化力量驅動,而意識的推動力一直在與無意識的隱秘欲望做鬥爭。

圖| Giphy
直到現在,我們的流行文化里還存在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比如電影《頭腦特工隊》。小女孩萊莉的無意識被禁錮在封閉的空間裡,其中充滿了「搗亂分子」和恐懼。正如電影的隱喻所示,人們傾向於認為那些不合適的想法和衝動都能被丟到無意識的空間裡,因為我們想相信自己的行為是有意識的。如果意識並不主導我們的行為,我們似乎就沒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然而,這種非此即彼的想法其實很不準確。近期的研究表明,大腦的意識和無意識過程不是相對的,它們並不樂衷於爭奪人類心理的霸權。事實上,人類的心智是一體的,意識和無意識相互交纏。即使是最理性的想法和行為,也主要歸功於自動的無意識過程。
大腦一直在做預測
我們的意識和無意識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一個革命性但已被廣泛接受的新理論——預測思維,有望提供一部分答案。

預測思維理論有各種不同的版本,但總體來說,它主張無意識過程是大腦思維的主角。這些程序讓我們儘可能快速和準確地預測事件。學習、經驗和有意識的思維不停優化著內隱(無意識)的預測,只有失敗的預測會引起有意識的注意力。也就是說,我們只對引起我們注意的情況有意識。這種自動化的預測讓我們得心應手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預測失靈時,我們的意識又能被及時喚醒,並根據環境調整策略,從而避免我們的自動預測系統掉入陷阱。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一個球朝我們飛來時,我們大腦中的無意識程序會預測這個球的運動軌跡,並相應調整我們四肢的動作。但如果這個球突然反常地轉了個直角彎,意識的程序就會被喚醒。
預測思維理論可以追溯到19世紀。當時的物理和生理學家赫爾曼·馮·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提出人類能根據感知而自動得出結論的假設。以視覺系統為例:我們可以輕易從三個被切了一角,並以特定方式排列的圓形中看到一個「不存在的三角形」。

我們的視覺系統通過想像出一個三角形來「解釋」這三個圓形為什麼被這樣擺放| Scientific American
亥姆霍茲認為,這種錯覺說明大腦記憶體在預編程序:不用做任何事情,它們就會自動形成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在當今的學術界中,預測思維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這種預編程序不只是決定我們如何感知世界,也同時影響其他心智過程,例如判斷、抉擇和行為。
為了讓身體正常運作,大腦需要快速而自發地區分身體本身的動作和來自外界的輸入。因此,大腦為每個發送給肌肉的指令創造了一份「感知副本」(efference copy)。舉個例子:當你前後搖晃頭部時,即使你所看到的世界在前後搖晃,你收到的感知副本會告訴你世界其實不在搖晃,而是你自己在主動搖晃。感知副本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撓自己的腳不癢:腳底板感受到「癢」的時候,大腦中的觸覺區域已經知道是你自己而非別人在撓了。
大腦多個平行層面同時工作
無意識過程的工作原理在很多現象中都有體現,例如自動運動、自發聯想和過早定論等。其中最有趣的一個例子,是所謂的「閾下刺激」——無法被意識探測的刺激。

根據預測思維理論,我們大腦中無意識和有意識的過程是同時發生的|圖蟲
為了探測閾下刺激是否能影響行為,科學家們已經做了一系列的實驗來驗證。通常來講,實驗人員會將圖片、文字,或軀體感受展示給被試,特定的展示方式能讓被試察覺不到刺激:要麼是因為刺激太短暫,要麼是因為刺激不在注意力中心。例如,心理學家會要求被試閱讀一段文字,其中某些詞會多次出現但並沒有被強調標註;隨後,對照組再讀一段普通文字。如果實驗組的被試在讀到之前多次出現的詞語後,表現出明顯的思維、感知和行為變化,研究者就可以假定那些詞語產生了無意識的影響。
關於閾下刺激的研究證實了我們「一腦多用」的能力。與電腦相比,腦灰質或許工作緩慢,但它能在多個平行層面同時工作。研究者們通常都會把這些工作分成兩種,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系統1和系統2。系統1包括所有快速、自動和不可控的無意識過程;系統2則包括那些更加緩慢、靈活和主動的有意識過程。不過在預測思維理論中最關鍵的是:這兩種過程其實是協力工作的。也就是說,我們大腦中無意識和有意識的過程是同時發生的。
下面這句話闡明了這個主張:普人通就以可懂讀段這話。雖然的字序順亂了,你是還全完理解,很易容就能懂搞句這話在說什麼。這是都為因大腦奇神的動自功能!
大多數人都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猜測出下一個詞語是什麼,因為我們腦中的「自動駕駛」功能在預測到下一個詞語時,就能很快地把打亂的字序排列整齊。
然而,在神經心理學的層面上,精確區分有意識和無意識過程一直是個難題,我們也並不了解它們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哲學家彼得·卡拉瑟斯(Peter Carruthers)認為,人類只能意識到自己工作記憶中的內容。但工作記憶只能勉強留住我們接受到的信息中很小一部分,並且這些信息很快就會消失不見。大腦接受到的絕大部分信息都不為我們所察覺,而是直接進入系統1被快速自動處理。

圖| David Firth/Giphy
大腦通過處理這些信息,就能自動回答一些問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可能會接收到什麼樣的刺激?有沒有什麼逼近的危險?其他人想幹什麼?這些預測不僅與外界相連,也與我們的身體和內環境息息相關。這樣看來,進食的欲望,只是大腦無意識地預測到了迫在眉睫的能量缺失。這些無意識過程致力於保持內穩態,讓我們的身體(包括能量攝取和消耗)保持平衡。
大腦如何做預測?
神經心理學家馬克·索姆斯(Mark Solms)十分支持預測思維理論,並對無意識與有意識功能有獨特的神經生物學解讀。他認為人類大腦並不尋求「更有意識」;相反,大腦一直在儘量地少用意識。他解釋說:「就像Talking Heads唱的一樣,『天堂是個啥都沒,啥都沒發生過的地方』。大腦就喜歡這種狀態,因為這樣能節省能量和時間。這是個生存機制。」
索姆斯在與神經科學家卡爾·弗里斯頓(Karl Friston)合作的文章里描述了他的觀點。十年前,弗里斯頓提出預測思維理論的數學模型,即自由能原理。根據該理論,腦中的自由能代表預測失敗時神經元的狀態;而大腦盡一切可能地避免自由能。在最終的分析里,索姆斯和弗里斯頓強調:預測誤差等於意料之外,也等於意識:當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時,我們才變得有意識——大腦竭力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這個觀點不僅完全反駁了弗洛伊德的理論,也與經典的「皮層為意識之源」的觀點相悖。索姆斯認為,這些高級腦區並不是意識的主宰,而是通過接收腦幹和中腦里更深層結構的「命令」來工作的。他還認為意識來源於掌管警覺、感情刺激和欲望的腦區——正好是弗洛伊德主張的無意識區域(見下方大腦插圖)。他說:「大腦皮層的規律檢測機制,在沒有意識參與的情況下,效率最高。更深層的情感腦區,即邊緣結構,才是意識的真正發源地。」

傳統觀念認為,皮層是高級心智功能的發生地。但是根據馬克·索姆斯提出的模型,意識來源於低級腦區,如網狀激活系統、腹側被蓋區和丘腦。只有當感覺信息(所有感覺信息都要經過丘腦)與情感或動機相關時才能被我們意識到,因為前額皮質和扣帶回皮質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導過去了。同時,紋狀體和楔前葉負責自動運動控制和定向,並讓我們得以無意識地就能與環境交流| Falconieri Visuals
索姆斯的理論有一定的經驗支持。比如,因為發育障礙而先天缺失大腦皮層的嬰兒,他們的大腦也可以進行特定的有意識過程;如果在進入兒童時期前沒有夭折,他們不僅會頭腦清醒,還能做出情感回應。在一篇2007年發表的綜述中,神經科學家比約恩·默克(Bj?rn Merker)總結稱,很多有意識現象的發生甚至不需要大腦皮層的存在。雖然如果沒有大腦皮層,我們就不能經歷更加複雜的心理過程,例如邏輯思考和自我反思,但我們還是能夠體會類似於喜悅、煩躁或悲傷的感情。
大腦真正的主人
很多人都固執地認為,本能的無意識和理性的有意識之間必定有清晰的分界——有意識肯定比無意識更好。但是,正如本文所述,這個看法是站不住腳的。無意識過程才在真正地控制我們的意識。你把注意力放在哪裡、你能記住什麼、你的想法、你要過濾掉接收的大量信息中的哪些成分、你怎麼理解它們、你的目標是什麼——這些都歸功於我們腦中的自動程序。

雖然我們對無意識的工作原理並不了解,但我們知道:它能將我們的身體運作得很好| Ben Sweet/Unsplash
社會心理學家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Wilson)認為,我們對無意識過程的依賴性,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生存下來所付出的代價。如果我們總是仔細考慮周遭情況中的所有細節,並比較每個可能的選擇,人類應該已經早早滅絕了。我們腦中的自動駕駛系統,而不是意識,成就了人類。
因此,解決問題和確保人類生存的真正總策劃,是大腦中的無意識。因為無意識是不可控的,所以人們對它缺乏信任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如果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影響我們,我們又怎能控制它?然而,雖然我們對無意識的工作原理並不了解,我們知道:它能將我們的身體運作得很好。
耶魯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約翰·巴奇(John Bargh)把人類心智比作一個水手:如果要讓船從A點行駛到B點,水手需要知道目的地,才能依此調整船的方向。但只能這樣還不夠。因為如同無意識一樣,洋流和風向等不可控因素也會對船隻的行駛產生影響。不過,專業水手在讓船駛向目的地的同時,也會把這些因素思考在內。
我們正確對待無意識的方法也是這樣——別擋它的路。當我把家人的照片放到書桌上,以此來激勵自己努力工作時;當我選擇走樓梯,而不是坐電梯時——我在引導我的無意識大腦,因為我知道:它想要娛樂和放鬆的本能,對當下的我並沒有好處。而我能這樣做,恰恰說明了有意識和無意識過程應該是搭檔,而不是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