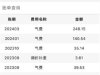一、從深層結構理解社會的底層邏輯
洪:我追隨您近10年的時間,幾乎每個文字都不放過。現在終於有機會得到這樣一個機會,把您過去40年時間的學術思想和脈絡,學習和梳理一遍。
孫:老實說,我非常感謝你。你那裡保存我的文章和言論,比我自己的都全多了。當然還有一些可能再也找不到了,比如搜狐微博時期的,特別是在搜狐博客上的。
洪:這些年在讀您的文章的時候,我特別關注您的方法論,一直在追尋文字背後的那種思想力量和洞察方法。我們今天就從方法論談起好吧?
孫:好的。在最近的一次講座上,我概括地談過方法論的問題。我是用三個詞來概括的:潛結構、長時段、宏觀背景與個人空間的彈性關係。講座結束後,參加講座的羅振宇先生和我說,還是用深結構比較好。我原來也想過這個詞,記得咱倆在海南還商量過,當時覺得這個詞沒怎麼有人用過,現在看還是深結構這個詞比較貼切,以後我們就用這個詞吧(見孫立平:潛結構、長時段:說說我的方法論)。
洪:類似的意思您在不少場合或文章中都講過。我的印象是,您特別強調社會結構的因素。怎麼理解社會結構這個概念?
孫:我們不從學術的角度說,從大家都能理解的角度說,社會結構就是在一個社會中的社會成員基於社會地位的高低形成的排列組合。在社會學中將這個叫做社會分層。這個東西在深層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重要(運用社會結構的視角對美國社會及大選的分析,見孫立平:六張圖詮釋美國的社會結構與對壘的陣營以及對人類文明前景的可能預示)。
洪:給我深刻印象的是,您曾經用社會結構的概念對市場甚至對產業周期做了一些很獨特的分析。您是從那時候強調社會結構這個視角的嗎?
孫:這裡有一個背景。在世紀之交的一段時間,我特別執著於一個問題:用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延長社會學的解釋鏈條。我的看法,社會結構就是這樣的一個核心概念。就如同經濟學裡的金錢貨幣、政治學裡的權力一樣。當時的想法就是將社會結構這個概念延伸到對許多重要社會現象甚至非社會現象的解釋。
最初的時候,想用這個概念來解釋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擴招的問題;接著用來解釋環境保護中的受益者和受損者不是一個主體而且力量不對等的問題。再接著,就是將社會結構的概念延伸到對汽車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解釋。這個我原來在一個音頻中系統講過,文字稿你那裡也有,就不細說了(孫立平:如何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問題)。
洪:這些領域還基本屬於社會學的領域,或者是社會學應用的領域。但對產業周期的分析就進入到純粹經濟學的領域了。
孫:可以這麼說。其實,對於經濟學我完全是一個外行。但有時候從社會結構角度觀察一下,也挺有意思。
你最近找我要的那四張圖,前三張就是傳統農業、工業化初期、後工業時代社會結構的圖形,最後一張是目前中國社會結構的圖形。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結構中,產業周期的過程是非常不一樣的。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理解中國的經濟為什麼會大起大落、短缺和過剩仿佛是一夜之間。就像有的朋友說的,我們不是穿短袖就是穿羽絨服,穿毛衣的時候很少。
洪:從這裡我可以理解您探索這個問題的完整思路。而且,在最近幾年中,您用這種方法對社會和世界走勢都有非常準確的預見,包括中美關係、拜登上台後對華政策的走向,尤其是對德國和日本轉變的預測更是顯示出先見之明。記得在默克爾執政對中國很友好的時候,您就預見到她任期結束後德國對華態度會發生重要變化。對俄羅斯最終會投向西方的判斷,雖然現在還沒到驗證的時候,但也提出了一種有邏輯性的推斷。這都是從深結構視角得出的判斷。
但從您這幾年對許多社會現象的分析,包括對世界局勢的分析,您深結構的方法論好像還不僅僅限於上面說的這個範圍。
孫:是的。在實際的分析中,深結構還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價值觀,一個是底層邏輯。我說的是我在實際中運用的,不是想給出一個關於深結構的理論框架。我不想在後者那裡多用精力。
洪:假如說,五年前,您文章中有關價值觀的內容並不多。但在最近幾年,這方面的內容明顯地多了起來。這體現了您對價值觀的重視。怎麼理解價值觀是深層結構的一部分?
孫:前面講的人們按照社會地位排列組合形成的,其實是一種狹義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社會學中使用的。但一個社會,整體上是由不同的因素構成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等,這就形成一種廣義的社會結構。作為文化一部分的價值觀無疑就是處在深層結構中。
在我原來的文章中,講價值觀的確實比較少,因為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似乎終結了,人們不講這個了,搞經濟掙錢就是了。但那個時候,我也不是沒有完全沒有涉及這個問題。比如,大約在10年前,我就曾經在微博上轉發過一位俄羅斯軍事評論員的觀點,他說,中國的一個弱點是缺少一種可以同其他社會特定階層進行對話的價值觀。
當然,在這些年,價值觀這個東西又突出出來了,我提醒人們要特別重視這個因素,不要以為別人眼睛裡只有錢。這次俄烏戰爭爆發後,一些西方大的公司寧可在經濟上遭受損失也要撤離俄國,為什麼?價值觀應該是重要因素。
洪:怎麼理解底層邏輯?您是什麼時候開始講這個問題的?
孫:我以前的一些分析,其實也往往涉及底層邏輯的問題,這樣,對社會的分析才能深入。但明確意識到這個問題,反覆強調這個問題的,是在孫正義停止在中國投資時開始的。我不記得是別人講過,還是我腦海中出現的,總而言之有這麼一個判斷,孫正義的舉動是基於他對底層邏輯置換的理解(孫立平:如何解釋孫正義的舉動:我一年多前就在講從資本逐利邏輯到安全邏輯)。
洪:看到您最近在幾個班上對這個問題的分析,講得更系統更深入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了解了這個,才能真正理解當今世界的變化。
孫:是的,我們現在可以說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無論是世界上,還是中國本身,都是如此。正因為如此,才有百年變局甚至千年變局一說。這個國內就已經講得很多。這個變局從什麼意義上來理解?我覺得最關鍵的是底層邏輯在變,也可以稱之為底層邏輯的置換。
從世界的角度說,我們面臨的底層邏輯置換表現為,後全球化時代的大拆解過程。在此前的全球化時代,世界的基本走向是一體化,世界在逐步成為一個地球村。而現在則是一個拆解的過程。拆成什麼樣我們還不得而知,是幾大塊?還是幾大塊加一些顆粒,抑或是一大塊加眾多顆粒?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世界的邏輯在變。我原來在這方面曾經寫過文章。支配全球化時代的是比較優勢邏輯和資本逐利邏輯,而在大拆解的過程中,安全的邏輯、價值觀的邏輯則開始起著更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的底層邏輯實際上也在變。最顯而易見也是大家最關心的,是財富邏輯的變化。大家都能感覺到近些年財富格局的變化。這背後是有邏輯的,最簡單地說,過去強調的是做蛋糕的邏輯,而現在則越來越強調分蛋糕的邏輯。同時,體制的邏輯、產業的邏輯也在變。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切的下面,是更深層邏輯的變化。
二、在對社會現象的理解中要加入時間和時段的眼光
洪:您講方法論的第二個詞是長時段。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第一波疫情時,您針對股市講的。
孫:那是2020年3月26日,我寫了一篇文章,《疫後經濟:悲觀但不絕望》。光看那幾個字,你會覺得那是什麼時候都可以說的廢話。但如果放到當時的背景之下,你的感覺就會不一樣了。有兩個背景,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大的背景是,當時的疫情在中國還沒有完全走出至暗時刻,在西方正開始水深火熱。內塔尼亞胡甚至說,他都想到了人類滅絕這個詞。有的經濟學家預判世界經濟可能會損失40-50%。小的背景是,一位小朋友給我打電話,股票已經虧了一半,問我怎麼辦。
洪:記得您當時給出的是補倉的建議。您對股票有研究嗎?還是基於其他的理由?
孫:其實我沒有直接給她建議,只是說如果是我,我會怎麼辦。我的建議,當然不是基於我對股市的理解,我哪懂啊?我是基於對歷史的了解以及看問題的方法論。
30年代大蕭條之前,美國股市的最高點是道指381點。在大蕭條中,最低跌到43點(1932年)。跌了多少?慘不慘?但如果那時候的股票拿到現在,又會怎麼樣?當然,前提條件是那個公司沒有倒閉,沒有退市。
這就需要我們有一種眼光,有一種方法論。大家都知道法國歷史學中的年鑑學派。他們倡導一種長時段的歷史研究。這種方法論不僅使得我們看股市的時候會有一種不同眼光,而且,看人類社會中的很多現象也會有一種不同的理解。當然,歷史學中的長時段概念和我這裡用的,意思不完全一樣。
洪:我的朋友中有許多是做企業的,長時段的方法論對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啟示?而且,企業必須將長遠與眼下兼顧起來。對於企業而言,怎麼處理長遠和眼下的關係?
孫:長時段只是其中之一,關鍵是要有一個時段的概念。大約七八年前,我曾經提出過一個說法:短期看政策、中期看趨勢,長遠看文化,體制貫穿始終。這時就經濟問題講的。所謂短期看政策,是說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行政主導的社會,政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況且我們還是處在一個政策的多變期。中期看趨勢,當時我講的主要是中國在經濟上面臨的兩個轉型。城市中是從大規模置業時代向後置業時代的轉型,當時我說大規模置業時代恐怕只剩兩三年的時間。你看看最近關於空置房的調查就清楚了。農村,則是在面臨溫飽階段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明白了這兩個轉型,經濟中的許多問題就比較清楚了。
至於長遠看文化和體制貫穿始終,就不詳細說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下面這篇文章:孫立平:用什麼來判斷中國經濟的走勢與前景?
洪:我在想一個問題,您這裡講的長時段與您在90年代末期提出的過程事件分析和實踐社會學是什麼關係?其中有沒有內在的聯繫?
孫:我記得在海南咱們見面的時候,你就好幾次提到過程事件的問題,你好像特別重視這個事情。從學理的角度講,長時段與過程事件講的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但你這個提問給我一個非常有益的啟發,我們可以嘗試一下在這兩個視角或方法之間建立一個聯繫。
過程事件強調的是,我們需要把許多社會現象看作是一個過程,很多事情無法簡單地按照既有的結構因素來解釋。舉個例子,在公共汽車上,就因為一個人不小心踩了另一個人的腳,最後雙方打得頭破血流。你說這個結果是哪來的?即使是這天公眾汽車上人多很擠,即使這兩個人脾氣都很暴躁,即使這兩個人頭一天都挨了領導的批評,即使這兩個人出門前都和老婆吵架了,即使眼看就要遲到了,也就是說,心情都不好,都很急,因為踩了一下腳,就一定會打得頭破血流嗎?不會的,沒有任何因素註定了最後一定是這樣的結果。那導致了這最後結果的是什麼?是事件發生過程中生成的新邏輯。
洪:這非常有意思。當我們把時間與動態引入到對社會現象的分析,看到的很多東西就不一樣了。不要以為這是學者的事情,我們普通人看社會現象也需要這樣的眼光。
孫:是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不能急功近利。一種眼光和思維方式形成了,很多事情就會觸類旁通。眼光和思維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為這些是虛的東西。
上個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我做現代化研究。開始的時候,我們往往都是將現代化作為一個結果,實現了什麼,實現了什麼,幾個現代化等。但在經歷了80年代末之後,使我意識到,必須將現代化作為過程來看,否則,很容易將事情簡單化。
這至少可以給我們帶來兩個洞察。第一,現代化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即使都是現代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間也是會有矛盾和衝突的,所以要研究現代化不同要素之間的關係。這一點,人們意識到了嗎?第二,同樣是在現代化中要實現的東西,在時間上可能也會有一個順序的問題,我們應當探討現代化的時序模式。這兩個問題我都專門寫過論文。
洪:這兩個洞察非常重要,就是用來看今天的問題,看今天的中國與世界,也會帶來深刻的啟示。
孫:是的。比如,很多人在講的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中美關係完全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當然是不行的,但不能否認這個概念還是有一定解釋力的。但如果把時間與過程的視角引入進來,你就會發現,需要把這個修昔底德陷阱看作是一個在時間上不斷展開的過程,不是一種靜態的矛盾或衝突。這樣看的話,會非常有意思。
再比如,現在關於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問題,人們對其效果有很多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價。給人的感覺是一團亂麻。制裁起不起作用?對戰事有何影響?對西方本身的衝擊有多大?西方能否承受?最後究竟會傷害了誰?其實,如果我們把時段的概念引進來,很多問題答案就會清晰起來。在短期的結果是什麼?長期的結果是什麼?分著看,就會清楚很多。
三、理解宏觀背景與個人空間的彈性關係
洪:8月24日,中國股市大跌。有人說是源於任正非的一句話:全球經濟長期衰退,要把活下來作為主要綱領。有人說,華為都把活下來做為主要綱領,其他企業就可想而知了。
孫:股市大跌的原因我還不清楚,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這形象地說明了,在一個不確定性的時代,整個社會是多麼的脆弱。有影響的人的一句話,甚至一個傳言,都有可能引起社會的強烈反應,而這種反應往往是過度的。但不管具體的原因和機制是什麼,其對億萬股民,對數千家上市公司的影響卻是實實在在的。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風險。
洪:所以這就涉及到您講的第三個詞,宏觀背景與個人空間的彈性關係。我最近見到許多企業家朋友,他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這樣變化莫測的大時代,企業和企業家如何生存?您強調的宏觀背景與個人空間的彈性關係,在現實中怎麼理解?
孫:就在前幾天,剛剛和一位朋友也是學生,聊到這個問題。說到宏觀背景與個人空間的彈性關係,他打了一個比方:在大樓倒塌的時候,很多螞蟻可能會生存下來。這個別誤會,不是說哪個具體的樓要塌了,這只是一個用來形象說明某種關係的比喻。確實是這樣,大樓倒塌的時候,不但螞蟻,很多老鼠也會生存下來。大地震的時候,很多小動物能夠生存下來。因此,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的大時代,做一個能存活下來的小動物。
洪:在我的印象中,您過去更多地是強調宏觀背景對個體的影響,得出的結論也是偏悲觀的多。但在最近幾次聊天時,我發現您現在好像更多地在強調個體的主動性的方面。這是為什麼?
孫: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感覺某種情況會來臨的時候,我當然要更多強調問題的一面,以對人們有所提醒,用任正非的話來說,叫將寒意傳遞給每一個人。比如在2018年的時候,我就提出中國有可能進入艱難十年。這樣的提醒是必要的,人們可以事先做準備。但當情況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時候,我們得換個角度來想問題了,我們應該怎麼辦?光焦慮是沒有用的。
第二,我在寫文章的時候,腦子裡首先想到的,是我的那些學生和朋友,他們很多是做企業的。每年和他們見面,吃飯也好,喝茶也好,聊天也好,可能不下上百次。因此我寫文章的時候,都小心翼翼。既怕過於樂觀誤導了他們,也怕過於悲觀影響他們做事的情緒。尤其是有的人四五十歲,正好是幹事的年齡,你說的人灰心喪氣,還怎麼幹事?正是因為這個,我一直強調宏觀背景與個人空間的彈性關係。也就是說,我們生活也好,做事也好,離不開這個宏觀背景,但宏觀背景與個人空間並不是完全重疊的。
洪:任正非講,未來十年應該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歷史時期,全球經濟會持續衰退。對未來過於樂觀的預期情緒要降下來,一定要把活下來作為最主要的綱領。但他同時也提醒,要有質量的活下來。問題是,怎麼才能活下來,尤其是怎麼才能有質量的活下來?
孫:確實,這是一個艱難的時期。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說,世界正面臨"重大轉變","我相信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轉折點或大動盪……我們的生活似乎是由一系列危機構成的,一個比一個嚴重"。馬克龍說,在這種情況下,法國面臨"犧牲",從前的富足生活將不復存在。在我國,在疫情中,大量企業關門倒閉。剛看到一則消息,說今年上半年有46萬家企業宣布倒閉,310萬家個體戶註銷。這其中包括一些在行業中排名很靠前的頭部企業。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活下來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前提。
洪:問題是怎麼才能活下去?
孫:儘管人們對任正非某些判斷還有不同看法,比如全球經濟是否處於持續衰退中。但我想,他提出的應對困難時期的一些建議和做法,應該是有價值有啟發的。他講了這麼幾條:生存基點要調整到以現金流和真實利潤為中心,不能再僅以銷售收入為目標,我想這也是他講的企業有質量活著的基本含義;盲目投資的業務要收縮,尤其是,未來幾年內不能產生價值和利潤的業務應該縮減或關閉;放棄部分市場;保住品質,保住質量。
洪:我理解任總的意思是,關鍵要保住企業的生存力。
孫:在一個不確定性的時代,生存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要有這種理念。我們經常說打不死的小強,應當成為這種小強。就企業來說,生存力的一個體現就是小而精。我們前面講過樓垮螞蟻在的例子。這個例子我們別往歪里想,其道理是很有啟示的。在樓垮的時候螞蟻為什麼能存活,老鼠為什麼能存活?前提是它的體積小。如果換做是大象,會怎麼樣?
上個世紀70年代的時候,有一本很暢銷的書,叫《小的是美好的》。作者是英國經濟學家E.F.舒馬赫。這句話我改變一下:小的往往更有生命力。
洪:記得大概是在2018年的時候,您就提出過收縮型社會和收縮型思維的概念。也許這是一個有益的思路。
孫:是的,是有這麼一篇文章。不知道為什麼被刪了。前兩天我又找出我講這個問題的音頻整理稿,在《孫立平社會觀察》公眾號上重發了一遍(見《孫立平:我們需要一種收縮型思維:我2018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在那裡,我說道:總體來說應當收縮規模,停止擴張型發展,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比較有把握的、將來有前景的有限的領域中,把這個事情做精、做好,這可能是將來立於不敗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
洪:我有許多企業家朋友,他們也想聽聽您的具體的建議。
對於企業我是一個外行,但我想,上面的原則大體是適用的。記得2020年的時候,一個做企業的學生給我打了一個很長的電話,就他想做的項目想聽聽我的意見。他介紹得很詳細。他說完之後,我就說,你的這些項目我一個也不懂。但有一個東西我聽明白了。什麼?就是這些項目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鏈條太長、環節太多。一定要知道:現在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時代,這些鏈條只要有一個地方出了問題,掉在這坑裡,爬都爬不出來。後來他說,您這兩句話,我非常受啟發。
2022-09-03Posted on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