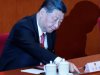【按:習近平已經將中國領回「政治上的延安」,在文學藝術上,中共本來就有一個「延安」,還出了不少好作家好詩人,但是從江胡到習近平,能出產的好文字只剩下順口溜了,所以中國文學也應當「流亡」到海外來了,是不是如此?便是我這個臉書帖子要討論的話題。】
我讀張愛玲傳記,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紐約,一日胡適到她寄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探訪,張愛玲後來寫成《憶胡適之》一文,內中寫道: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的驚訝,不止在寫盡十里洋場脂粉氣的這位「海派祖師奶奶」,筆下竟也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這樣大氣的文字,還在於當年她是以難民身份從香港申請來美國的,也就是說,一直被視為抗戰十年躲在上海孤島摹寫痴男怨女、淒涼喧囂的張愛玲,後來是一個躲避共產制度的政治難民,只是張傳的作者們,彷佛有默契地不去聲張這一點,好像它有損於張愛玲隆重的身後盛名。其實張愛玲的小說,和她的淪陷區經歷,以四九後中共的邏輯來看,無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一、「逃離沉船」與恐懼的異化
實際上,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其間。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八九六四之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裡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二、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Asylum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庇護」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里,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三、「六四血卡」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庇護,我自己也卷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卻一直沒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寫出什麼感受和困惑來,雖然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的「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
獲得「庇護」乃是「占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裡去,折騰得面目全非。
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
四、有沒有「避難文學」?
這個話題從張愛玲說起,便牽扯到文學,而「六四血卡」這個說法,脫胎於魯迅的「人血饅頭」,頗有象徵意味,與其說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說它更具文學性,十萬之眾的「綠卡大軍」,錯置於中西文化的歧義、衝突之間,背後豈能無故事?由此而引出一個關於「避難文學」的提法,也許值得討論。
著名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詮釋中國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指出其異國情調與懷鄉姿態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留學生出國、歸國和去國的行止,不止顯現留學生個人的價值抉擇,也暗指了整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歸與不歸的問題,在以後的數十年仍將是海外學生揮之不去的心結,作家將其付諸文字,也成為中國小說『感時憂國』症候群的特例。」他將魯迅、老舍、郁達夫、冰心、錢鍾書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學生文學」,並指出他們「上承晚清留學小說的遺緒,下開六、七零年代白先勇、於梨花、張系國等人新留學生小說的先河」。
當「新中國」變成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又因人口龐大,留學、流亡再次使「逃離」成為時髦,但再無「留學生文學」,卻展示了「六四綠卡」、「人血饅頭」等另一種「避難文化」,或許會令郁達夫等汗顏。
核心問題是,中國人被洗腦之後,最大的困境乃是無法剔去「國家」,重建「個體」;沒有個體,哪來文學?哪怕個體還在中西錯亂、衝突之中,也會出很好的小說,我想大概小說也寫了不少,然而能出版的並不多、質量高的就更少,王德威說的「以留學生為題材的作品曾經形成一小傳統」,假如在今日如此龐大的中國留學生、洋插隊、洋打工、走線、逃難群體中斷了線,那可真是無顏以見江東父老!
轉:

張潔平
最近令我深感震撼和啟發的一本書。以前我一直好奇,為何對百萬中國人逃難至台灣的這段歷史的理論書寫這麼少、學術研究這麼邊緣。楊孟軒老師這本書,令我明白一二。研究有許多令人深思、非常精彩的亮點,尤其是對離散過程與概念的反覆辨析、再造身份的「記憶體系」、創傷研究中「多向同理」。
研究者的研究起點,同樣動人且唏噓。我抄幾段在下面,有機會再寫更多筆記與訪問。向所有的歷史創傷二代、三代,或是正在親歷著歷史與政治創傷的人,強烈推薦這本書。

本周日(明天)下午,楊孟軒老師在飛地,分享這本研究的前前後後。萬勿錯過
摘錄:
/////我生長於台灣中部台中市的一個閩客聯姻本省人家庭。父母雙方的家族都深受二二八事件所害,但他們選擇遺忘過去、展望未來。母親和父親辛勤工作、努力存款,1990年代移民加拿大。我才十來歲就離開台中前往多倫多,那時是李登輝總統任內,台灣正著手開展政治、社會、文化的重大轉型。這一切石破天驚的變遷,對於那時的我其實沒有多大意義。我和多數青少年一樣,只在乎運動和電腦遊戲。離開台灣這些年,我回去探望過家人和朋友幾次,但我的人生在加拿大。我幾乎沒有留意過台灣社會、政治、學術進展,直到成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在2004年重返這座島。
2004年返台之旅真是大開眼界,我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即使比外省人的漫漫歸鄉路輕微得多,情況也不同。台灣的一切看來都這麼熟悉,卻又如此陌生。這個年輕民主國家的眾聲喧譁、活力充沛令我著迷,感到無所適從,卻又莫名興奮。即使如此,不斷加劇的政治對立和族群緊張卻也讓我深感不安。在進行研究,準備撰寫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碩士論文時,我速成學習台灣多層次的殖民與移民歷史。我的研究帶來一些令我震驚的個人發現。
我發現二二八事件屠殺期間,叔公是在宜蘭縣遭蔣介石軍隊處死的本省人菁英之一。此外還得知,國民黨政權也在二二八事件過後把外祖父囚禁在綠島多年。我的外祖父曾是舊日本帝國軍人,太平洋戰爭期間在菲律賓打仗。國民黨當局把他和其他許多台灣籍前日本皇軍一期逮捕,指控他們在二二八事件抗爭期間武裝反抗政府——阿公當然沒有做過這種事。
這些揭露出來的事實令我震驚。我又氣憤又難過,質問雙親為何把這些事全都瞞著我。父母對我說,他們這麼做是為了姐姐和我好。「你改變不了發生過的事,」父親說:「再怎麼去想也沒用。最好就忘掉,放下一切吧。」
我知道不可能責怪父母、姑姑、阿姨和叔伯、舅舅,更不可能責怪祖父母或其他長輩的不曾告知⋯⋯
我把滿腔憤怒都指向國民黨和外省人。這個研究計劃部分是被一份使命感所驅動,就是揭發外省人來台之後對本省人做過的所有壞事。儘管如此,當我對大出走了解愈多,對中國內戰和整個台灣歷史了解愈多,便對外省人開始產生強烈同理心。身為移民,又是如今在美國工作的「一點五代」台裔加拿大人,我知道身為局外人,身為離散主體是什麼滋味。
我也逐漸體認到一個事實:我的遠祖在清代從中國遷移到台灣,他們對於島上的原居民同樣是掠奪成性的殖民者。我所屬的族群如今很多人稱之為「本省人」,他們也經由土地掠奪、通婚、種族屠殺和強迫同化,大舉消滅台灣在地的南島民族群體和文化。
這個學習過程一點都不容易;它漸進、曲折、矛盾又令人不安。我被互相衝突的情緒,甚至不時發作的抑鬱所困擾——因此造成好幾回寫作瓶頸,對這項智識計劃的更廣泛意義也變得不確定了。
⋯⋯我深思一項艱鉅任務:陷溺於各自歷史創傷的憤恨不平、自以為義或崇高氛圍之中的不同記憶群體,如何修復關係?
⋯⋯個體和群體站出來表達悲傷,亦即台灣本地人所謂的「悲情」,以尋求認同、自我肯定和他人的認可,這樣的過程迄今未能帶來建設性的對話。即使運用創傷這一共同語言,人們卻不曾真正交心,述說的故事也從未真正彼此產生共鳴。兩次重大的文化創傷將民主化台灣的兩大記憶群體分隔開來:半日本化台灣人後裔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布,亦即中國內戰流亡者後裔的大出走。⋯⋯
閱讀拉卡普拉之前,我以為對自身家族創傷的持續依戀,和對有份造成家族創傷的那群受摧殘的流亡者愈來愈深的同理之間的內在掙扎是道難題,甚至是累贅;但讀過之後,我開始換個角度看問題。⋯⋯首先,我沒有被大出走記憶的情緒重量牽絆住,並成為外省人的代言人(從而運行一套排解且未經調節的「宣洩」模式),我在開始考察時反倒毫不同情,甚至懷疑外省人的創傷——有鑑於上述個人背景,這是可以理解的。我沒有記錄和推廣他們在當前述說的悲傷故事,而是鑽研檔案,試著理解過去究竟發生什麼事。研究和內在衝突將近十年後,我逐漸對外省人產生居間促成且通曉歷史的同理。其次,我所獲得的知識和視角則翻過來緩和怨恨感,並緩慢而確實地創造出某種批判的距離,把我對自身家族創傷的忠誠區隔開來。到頭來,研究外省人和撰寫本書,在這兩個互補的方向上成了一種個人「修通」過程。
⋯⋯我把我所提倡的越界模態看成一種倫理責任,其為研究與書寫歷史創傷的基礎所在,特別對於未曾真正經歷過那些創傷的研究者而言。
正如拉卡普拉所說,相較於真正經歷過暴行、迫害和流離的先人,有幸「晚生」於更好時代的我們必須接受一套不同的倫理要求約束。我們必須意識到,就連最親愛的人所受的磨難,都不可能是自己的苦難。二手見證和替代性創傷所產生的影響可能強烈、令人不快,有時還能激起憤怒,但絕不可能和真正的創傷事件同樣強烈。因此,參與研究和再現歷史創傷的學者、作家、藝術家、電影工作者和線上內容創作者,都有一份道德責任,不要沒完沒了地沈溺於自己的悲苦,要超越既有的分界線。
歷史並非治療歷史創傷的萬靈丹。但尋求同理、和解,乃至被痛苦記憶撕裂的群體和國族都能接受的轉型正義途徑,其可能性卻源自一種通曉歷史的理解,並以適當視角看待這些記憶。/////
——楊孟軒《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P309-327
出版社:台大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