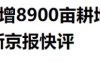【按:標題是陳雲之語。當下普京侵烏敗跡顯現,向習近平求援,以中共奉俄為師的歷史,援俄勢在必行——俄烏中三國曾有一種歷史脈絡:史達林在烏克蘭製造大饑荒、毛澤東學史達林搞「大躍進」,餓死中國人四千萬,已經是陳雲給出數字的一倍,這次再拉上中國為俄羅斯陪葬,看來也是勢在必行,可樂觀其成,雖然中國人又要賠上性命。借我新書上市之際,再說說中蘇兩黨的傳承,雖然本文『《「烏托邦」祭》日譯本序言』並未收入此書,它寫於三十年前。】
一、
這本描寫中國「大躍進」的長篇紀實作品,是1988年初我一拍完電視片《河殤》後就立即著手寫作。寫這本書的動議,最初是由江西《百花洲》雜誌社(廬山在江西境內)提出的,他們為我找了兩位合作者,羅時敘和陳政,都是廬山地區的作家,關注和研究廬山會議事件已有十年時間。沒有他們的參與,這本書是寫不出來的。同時,我們也得到了一些廬山會議親歷者、研究這個事件的專家的熱情幫助。書稿由《百花洲》雜誌刊登,但在發行前遭到北京高層的查禁,只有零星雜誌在社會上流傳。後來在1989年,這本書由一位個體出版商靠「地下渠道」印刷發行,在全國一時風靡,此時天安們事件已經爆發。
「大躍進」主要包括了全民大煉鋼鐵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29—1933年的蘇聯集體化運動導致了嚴重的饑荒,致死人數估計達一千四百五十萬。中國大躍進運動的後果,比蘇聯要慘烈得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它又成為引發更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個淵數。我們對這種因果關係的研究還很不夠。
海外對大躍進所致之饑荒的研究,已有著作和文章。但因資料所限,僅能根據中國人口的總的數據,推斷出全國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數據。另外,由於中共對這段歷史深為忌諱,一直不開放擋案,也深怕中國大陸的學者和作家染指這段痛苦的往事,以致對這次在中國歷史上都很罕見的大饑荒,學者們所能提供的結論便只是幾個抽象的數字,諸如一千萬或三千萬之類。饑荒之空前慘烈,幹部之非人道,政府救災之不力,以及人性之泯滅都隱沒在幾個數字之中。
從大躍進的發生和後果可以看出,第一,共產主義這種天方夜談實際上多走一步就是鬼域世界;第二,中共政權在不發達的條件下,掠奪得最為兇殘徹底的對象,偏偏是它所賴以奪取政權的基本力量—農民;第三,當領袖、黨的意志和利益高於一切,人民皆為芻狗,吃飽肚子的權利和其他一切權利都不可能存在,歷史已經證明過,中共是一個連人們吃飽飯的權利都要剝奪乾淨的非人政權。
二、
發動大躍進的政治背景,起初只是中共高層關於中國大陸發展方向的鬥爭,也可以說,是中共試圖以超高速的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爭的一種現代化嘗試。鬥爭的結果,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激進的「烏托邦」思潮和好大喜功的熱昏情緒占了上風。但試驗的結果,卻是激進派的失敗。失敗引起黨內權力之爭,並進一步導致瘋狂的蠻幹,直到餓殍遍野才止步。這地地道道是一場人禍,而絕不是自然災害。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採取了蘇聯史達林式的發展策略,即利用計劃經濟結構,優先發展重工業(包括軍事工業),尤其是要獲得鋼鐵。這種發展導向,自然是由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格局所帶來的,其中不僅有韓戰和台灣的因素,在中共領導人的戰略考慮中,還有對蘇聯的隱憂和防範。所以,毛澤東的急功近利,並非都是浪漫情調,而有其嚴酷和現實的政治需要。
發展重工業所需的資金,自然也是學蘇聯,由政府通過徵收農業稅和工農業產品價格上的「剪刀差」取得。然而,中國當時的農業,基礎要比蘇聯差得多,1928年蘇聯糧食的人均產量是566斤,而1957年的中國只有290斤,因此,中共榨取農業「剩餘產品」的餘地要比史達林小。再者,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共是靠農民革命得天下的,它在農村的政治基礎使得它不能完全效法史達林1929年的野蠻做法。事實上,當時的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政治局候補委員),就曾彙編蘇聯1929年強行集體化造成惡果的資料送回北京,委婉的提醒毛澤東不可蠻幹。
1957年11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受到赫魯雪夫提出蘇聯在十五年內趕超美國的口號的影響,也當場提出了中國要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的口號。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集體化和大躍進的問題上,都是亦步亦趨跟蘇共學來的。這既反映了共產主義在發展模式上並無各國可以選擇的自己的道路,毛澤東除了搬抄蘇聯是沒有自己的創見的,也反映了毛澤東好大喜功的性格使他只會比蘇聯作得更過火。
三、
毛澤東用來強迫黨內外同意他搞「大躍進」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一再強調中國農民「天生具有進入共產主義的衝動」,不同意他這種看法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就是「小腳老太婆」。毛澤東經常借用「人民」這根棍子來壓制不同意見,他常常愛說得一句話是:八億人民泄了氣怎麼得了?
後來他乾脆到《三國志●張魯傳》和陶淵明的詩里去找所謂中國人的共產主義「原始根」。他說東漢末年的五斗米道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雛形,信教者出五斗米就是公共食堂,「置義舍」就是公共宿舍,「以神道治病」就是免費醫療,「以祭酒為治」就是政社合一,等等,這一派似是而非的說法,由於以所謂理想、人民等最崇高的理由作幌子,竟使人們不能質疑。
但實際情況卻完全相反。中國農村從1951年開始搞互助組,起初還是提倡自願,從1953年底開始,政府就逐漸對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和油料實行統購統銷,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打擊和嚴禁自由經營糧食。在收購時,許多地方還對未入社的農民強迫多征。僅1954年,全國就比計劃多征了一百億斤。事實上,從1952年2月毛澤東為《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序言以後,中國的合作化運動就已經是一場剝奪農民生產資料的政治運動。
據當時官方公布的數字,1955年底,農業合作社在全國還不到兩萬個,入社農戶只占總農戶的百分之四;但到1956年底,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如「雨後春筍」般擴展到76·4萬多個,入社農戶1,1674萬多個,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六點一。在這些數字的背後,是普遍的強迫威逼。早在1952年冬的互助組「熱朝」中,不少地方就已強迫農民把農具、牲畜充公,連棺木也入了社。幹部威脅農民說:「誰不入社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
本來,毛澤東自己估計合作化運動要用十八年時間完成。他並沒有想到用這種野蠻的手段剝奪農民如此容易,便愈加昏昏然。但是,黨內對這種「強迫命令」的「急躁冒進」,卻大有反對意見,最主要的人物偏偏是主管合作化運動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他在1953年已經被毛批判為「犯了右傾錯誤」。1955年他再次反對毛主張立即將合作社的數量「翻一番」的意見,很快就在十月的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被撤職,黨內並展開一場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整肅運動,一大批對如此野蠻剝奪農民有意見的黨員、幹部被批鬥、撤職;黨內鬥爭又迅速擴展為全社會的大整肅,全國大抓「小鄧子恢」,各地「拔白旗」(未入社的農戶)花樣翻新,把五年前分田地、鬥地主的那些手段都用上了,也可以說,十年後的「文革」已在此時預演。
經過這一場以恐怖為前提的鞭打驅趕,中國農民便默默接受了剝奪。大躍進的心理基礎已經奠定。然而,集體化以後,中國糧食的增長速度反而降低了。1953—55年,糧食增長速度超過百分之四,到1956—57年,已低於百分之三。農民沒有公開反抗剝奪,他們先是搞瞞產私分、濫宰牲畜,繼而讓大量糧食爛在地里不去收割,最終這些都抗不過了,他們便開始撒謊虛報產量去糊弄乾部,幹部也以此去糊弄毛澤東了。這就是大躍進年代那些「高產衛星」的神話的由來。
1958年元旦剛過,毛澤東就在南寧發出大躍進的號令。到夏天,他又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決定並公開宣布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530萬噸)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全國立即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這是大躍進的癲狂期,據當時官方的統計,兩個月里,全國投入近一億人,城市和農村建了六十多萬個土高爐,大片森林被砍伐,大量礦山資源被破壞,耗費如此巨大人力物力,1958年的鋼產量里合格品只有800萬噸,含硫量極高的土鋼土鐵達416萬噸。
與此同時,農村強迫徵購糧食的「共產風」也更加劇烈。政府估計1958年全國糧食總產約8,200億斤,於是下達的徵購指標高達1,175億斤;事實上,產量只比1957年增長了百分之二點五,而徵購指標卻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三。
大煉鋼鐵和高徵購,打亂了整個國民經濟,市場供應短缺,北京市每天一人一兩蔬菜。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當時的糧食部長陳國棟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告訴他,全國儲備糧只剩下330億斤,平均每人只有50斤糧食,各大城市紛紛告急,而農民已經在吃糠咽菜,農村無糧可征了。
其實,早在1956年相當一些地區已經發生災荒。如安徽省的人口死亡率突然由1955年的千分之十一點八增加到1956年的千分之十四點二五。廣西省已經因災荒餓死人,省里對此漠然無視,造成1,4700多農民外逃,550多人餓死。1957年上半年,廣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北京、山東、河北、遼寧等省也都有大批農民上訪要求退社。但是,在這年夏天毛澤東、鄧小平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後,農民的抗拒很快退縮了。
四、
整個大躍進時期,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至今還是個謎。據近幾年中國政府公布的數字,是兩千多萬。這基本上同西方學者根據人口資料測算出來的數字吻合。筆者認為,這只是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的一個數字,離真實還有一段距離。筆者曾請教過一位大躍進時期在安徽工作的中央幹部,他說安徽的死亡數字有三種:一是二百萬,一是四百萬,一是八百萬,看你願意相信哪一個。曾經受中央委託作過全國農村調查的前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所長陳一咨先生告訴筆者的數字是:
四川—九百萬;
安徽—八百萬;
河南—七百八十萬;
全國—四千萬以上。
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之際,中共元老們曾有一句名言告知天下:我們的政權是用兩千萬條生命換來的,誰想拿走,就用兩千萬性命來換。
儘管這個政權標出的價碼如此駭人聽聞,但它還是沒有把1949年以後的成本算進去。因為或許連中共自己也知道,倘若1949年以前的那兩千萬條生命,還能勉強算作是老百姓情願為共產黨付出的犧牲的話,那麼,1949年以後的無數「非正常死亡」則是這個政權強迫人們付出的。這些生靈的無端喪失,只能被視為這個政權的罪惡。即使按照中共的邏輯,他們的政權可以拿人命去交換的話,苦難深重的中國人也早已付出了超出幾倍的價碼。
最後,我要特別提到辻康吾先生,是他把《河殤》譯成日文,如今又把這本書介紹給日本的讀者。他讓我深感日本學者的執著和認真。我也向參與這本書翻譯的其他日本學者表示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