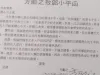京戲大師程硯秋多次遇見過我,但他不認識我。我見到大師的次數,同大師遇見我的次數一樣多,對等。所以,不是由於看他的戲。若是看戲,台下看得見台上的,而台上一般看不見台下的,不對等。我在北京數十年,從來沒有買票進戲園子看京戲,因為聽不懂。京戲的「京」字容易誤導,以為它是基於北京及其周邊的方言的戲曲。其實,京戲是南腔北調的大雜交,再加上唱腔抑揚婉轉,結果,我對京戲唱段中的吐詞咬字的分辯率,最多達到 50%。
按北京話,看戲不叫看戲,而叫聽戲。聽比看更重要。所以,聽覺解析度低者,就無緣欣賞京戲了。當然,並非所有生長於北京的人均如此,我這類應屬於少數。在小學同學中間,大概不超過49 %吧。不論聽不聽戲,在北京(1945年之前,1949年之後)或北平(1945-1949年),四大名旦之一程硯秋,無人不知。
1945年8月暑期,抗戰剛勝利,我的小學五年級已結束,成績又是甲等第末,乙等第一。當時,每學期末要在學校門口張榜公布學生名單,以成績優劣為序,我的名字總是緊貼一條線,該線以右者為甲等,以左為乙等或乙等以下。
開學後即將升入六年級。就到小學最高班了,很得意。那時我九歲。九歲可不是一個值得得意的年齡。社會上(至少在北京),有一種傳統的年齡和性別歧視。
俗語云:「七歲八歲討人嫌,到了九歲饒一年」。
其意是,七,八,九歲的男性小兒是最討厭的,少招惹他們。現在想想,七,八,九歲時的「榮辱觀」(借用此詞)是有點 「反常」。如果一項不軌行為能惹得大人討厭,或挨罵,不但不會感到灰溜溜,反而有一種成功感。瞧!我有能耐吧,我能惹大人開罵了。所以,不軌行為常是蓄意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挨罵時的快感。
當時我家住在西四北報子胡同25號。我上的小學是「北平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簡稱師範附小)。校址在報子胡同14 號。現今的網頁上說,該校已改名為西四北四條小學。而且說,該校前身為八旗子弟小學之一「正紅旗官學」,建於1883年。在我上學時,還看得見的「官學」 痕跡是,高小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即使貴為滿清遺族格格,也不收。
報子胡同里,單號路南,雙號路北。14號就在25號的斜對門,出我家門向右斜走約二十公尺就到學校了。
大師程硯秋住在報子胡同18號。也是斜對門,出我家門向左斜走約二十公尺就是18號。程家的黑門總是緊閉的。只當大師的鋥光瓦亮的專用人力車進出時,黑門才大開。那種人力車,是北平當時的豪華車,相當於今天的寶馬、奔馳。
小學裡的「討人嫌」和「饒一年」們,經常在師範附小門口附近(也就是我家門口附近)瘋玩兒,消磨多餘的能量。所以,常與大師不期而遇。大師對我們從無任何表情。在大師的眼裡,我們不存在,就如眼睛沒有聚焦。我們也沒有看到程氏與周圍的鄰居和師範附小的老師或校長有交往。
嘿嘿,「行為不軌」的下一個目標有了。程家的黑門上有個電鈴,是為訪客用的。當時有電鈴的人家不多。有一位「討人嫌」建議,我們去摁程家的電鈴。摁後,快速跑回25號門後,觀其反應。第一次,程氏的傭人出來開門,沒有看到訪客,以為是偶然事件,沒說話,回去了。我們沒有成功——沒有聽到罵聲。
再接再厲,等傭人回去後,我們再去摁電鈴。再快速跑回。程氏的傭人又出來開門,又沒有看到任何人。這一回,他明白了,一定是這一帶的「討人嫌」和「饒一年」團伙乾的。程氏傭人看不見我們,就站在18號門外,對著當街破口大罵(所以,北京人一般不稱罵人,而稱為罵街,罵大街等等)。我們都藏在25號門後,聽得見罵聲,享受著聽罵的快感。我們也可以從大門門縫向外窺視,欣賞罵街者的臉色變化,有趣,禁不住地竊笑。如此往複數次,都很成功。
再後,又不行了,既便摁了鈴,也沒有人出來開門罵街,因為程氏門房猜到,又是這一夥「討人嫌」搗亂。
為了迫使程家人出來開門,我出了一個主意。當時北平在修馬路,報子胡同口上就有修路用的瀝青。瀝青有黏性,導電,但變形十分慢。我們找了一塊比電鈴略大的瀝青,照准程氏大門上的電鈴猛力糊去。這樣,電鈴就一直在被摁狀態,鈴聲不止。果然,有人出來開門了。一看又沒人,但電鈴還在響。再一看,電鈴上黑乎乎的一片瀝青,愣了,不知所措,竟然不敢動,也忘了罵街。其實,只要把糊上的瀝青扒掉就行了。程家的傭人也許怕有電,他們可能沒有機會聽過小學的常識課。
小學老師早就給我們講過預防觸電的常識:「電燈的電壓是220伏,不能用手摸,有觸電危險;家用電鈴在20伏以下,沒有觸電危險等等」。當時並不懂電壓,伏和歐姆定律的真諦。但記住了電鈴的電對人是安全的。我有一本「少年電器製作法」(中國科學社,民國27年出版),也講電鈴的製作。
程家傭人一定會稟報程大師:「電鈴騷擾事件」是鄰居中的「討人嫌」和「饒一年」一夥乾的。程氏卻一直沒有到周圍鄰居和師範附小追究此事。還只是當他的豪華人力車進出時,我們才能看見他。大師程對我們依舊沒有任何表情,水晶體依舊沒有聚焦好,在他的眼裡我們依舊不存在。
程氏沒有追究「騷擾事件」,原因之一也許是,京戲名伶,那怕是有錢的大師,在老派北京人(如正紅旗或其後裔)的眼裡,社會地位並不高,甚或很低。這些老派北京人常講,「朝廷召徽班(京劇前身之一)入京,那是來給萬歲爺解悶兒的,在宮裡演戲,是太監的活兒。」其意就如時下的「正紅旗及其後裔」, 視專用於解悶兒幫閒兒的「文化人」「吹鼓手」為其包衣吧。
大師不追究,我們也就不騷擾了。大盜亦有道,何況小兒騷擾乎。
夏天過後,「討人嫌」和「饒一年」團伙自動解散。除了上課,我的剩餘能量也漸漸地轉移到安裝礦石收音機上(後來進步到真空管收音機)。礦石機的安裝調試很費時,有時弄到很晚,父母及兄妹們都睡了,我一人在靜夜裡奮鬥。一當礦石機在靜夜裡突然發出聲音,興奮至極,其快感,比挨罵大有不同。
礦石機只能收到一個台——國民政府的北平廣播電台。該台除了少量時間播報新聞外,大部分時間是放送上海百代公司的京戲唱片,夜間尤其如此。所以,每次礦石機收到訊號,十有七八是程硯秋等大師們的京戲。
作為玩收音機的一個副產品,我聽過不少西皮二黃,甚至還說得出各大師們的招牌劇目,如程大師的拿手戲是「鎖麟囊」,著名唱段的頭兩句好像是「春秋亭外風雨暴,何處悲聲破寂寥……」但因注意力始終是在收音機的裝——調——修——拆——再裝——再…,不記得是西皮東皮風雨暴,還是大黃二黃破寂寥。所以,至今真正能聽懂的京劇唱段中的咬字吐詞,依舊停留在50%的水平上。半吊子之謂也。
供辛卯除夕一笑,2012.1.22,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