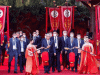盛唐時期中國地圖
公元八世紀中葉,世界上三個超級大帝國,唐、阿拉伯、吐蕃,經過了近百年的擴張之後在中亞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著名的怛羅斯之戰便於此時爆發。由於史料的簡略和戰爭的重要,歷來學界對此頗為關注,且各持其理。
怛羅斯[1]之戰是中國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蔥嶺以西的強大帝國交戰,也是古代史上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唯一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其結果是以中國人的失敗而告終。怛羅斯一役,幾萬唐軍死傷殆盡。那麼,為什麼處於極盛的唐帝國會敗的這麼慘呢?這場戰役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對歷史有何影響?
對這場重大戰役的研究,已經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了,早在四十年代,白壽彝先生就開始撰文論述,指出此役是唐帝國在西域霸權的沒落的徵象[2],之後陸續有學者對怛羅斯一役進行論述,九十年代,尤以北大王小甫先生的專門著述較為詳備,認為怛戰是一場遭遇戰,阿拉伯帝國方面的主流政策是和平的[3]。但隨著近年來史學研究的進步,對於此戰,學界有不同的聲音,張晶如先生從中亞突騎施姓氏派系鬥爭角度來解釋戰爭爆發的原因[4],李方、王三義等學者對邊將高仙芝的個人行為多有譴責,但李方認為戰役雖出於偶然,卻是唐與阿拉伯帝國衝突的必然結果,王三義先生認為阿拉伯上層實施的是和平政策,怛戰是邊境上的意外衝突[5],張晶如先生觀點相反,認為怛邏斯戰役的發生是大食帝國疆略政策的繼續。至於戰後文明的交流和技術的傳播,以往學界一直堅持是怛羅斯戰役的貢獻,近幾年有烏茲別克斯坦學者在研究中指出,怛戰之前造紙術就以和平的方式通過大唐治下拔漢那首府浩罕傳往撒馬爾罕[6]。另外多數學者大談和平,大講戰役交流的一面,而對戰役雙方的衝突與對峙有所忽視,這必然會使學術研究準確性與客觀性有所降低。因此,對於上述各種觀點,筆者有的贊同,有的實不敢苟同,下邊我們將從怛戰前兩大帝國的對峙與衝突,怛羅斯之戰的經過,唐軍慘敗的原因及影響等方面進行再探討。
一、怛戰前兩大帝國的對峙與衝突
我們知道唐阿這兩個超級大帝國幾乎是同一時期建立並通過對比他們自身更強大的帝國進行征服而逐漸壯大的。公元618年,李淵建立大唐帝國,到高宗時期,擊敗了突厥人、高麗人、安南人,臣服了西域諸番,形成了東至太平洋,西及波斯,北至西伯利亞,南到中南半島的空前大帝國。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受真主阿拉的啟示創立伊斯蘭教,至661年哈里發建都麥迪納,大舉擴張,侵入波斯帝國,掠奪了拜占庭帝國的半壁江山,征服了敘利亞及北非的大片領土,形成了橫跨亞非的龐大帝國。
642年尼哈溫大戰,阿拉伯人殲滅波斯的大部分軍隊,651年波斯王在流亡吐火羅途中被阿拉伯兵擊斃,之後其子卑路斯向唐求救,唐阿兩國正式接觸[7],但此時沉陷於阿使那賀魯叛亂的唐軍根本無力支援。卑路斯只好在吐火羅的支持下復國。此後,波斯又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並再次向唐朝求援。《新唐書》卷221《波斯傳》載:「龍朔初,(波斯)又訴為大食所侵。」是時阿史那賀魯叛亂已被平息,唐已接管西突厥汗國在中亞地區的轄地,因而開始介入波斯事務[8]。唐朝在波斯置都督府,將波斯納人唐朝的版圖,置波斯於唐朝的保護之下。龍朔二年(662)正月,唐又正式宣布「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9],支持波斯復國。唐朝對波斯的態度,無疑是對阿拉伯人侵的對抗,但這種對抗是政治行為,而不是軍事手段。663年,波斯再度失國。王子卑路斯避難長安。徒具虛名的大食安撫使[10]裴行儉以幫助波斯復國為名,奇襲阿使那都支叛軍,並沒有到達波斯,更談不上與阿衝突。事實上,唐在中亞的統治從一開始就屬於荒服來賓的狀態,此後大食占據了其波斯都督府所在疾陵城,併入侵吐火羅,臣服康、石諸國,唐政府並非不知[11],但此時的唐帝國正全力與吐蕃人在爭奪西域,對阿拉伯這個遠在遙遠的西方的龐大帝國的征服無可奈何。
直到670年,大食人所到的最東之處還在吐火羅西部和塞斯坦[12]。正如王小甫說的那樣,此時大食人在中亞的征服結果多半是「講和」,儘管總是在退走之前進行了大量的勒索[13]。直到名將屈底波出任呼羅珊總督時才開始有了「攻克」。也正是屈底波強硬的征服政策,使阿拉伯帝國在東面的勢力達到了頂峰。他們控制了印度河流域、吐火羅,進而北上將烏滸河流域納入其勢力範圍,又與唐合兵擊潰了此時橫行中亞的突騎施。西方學者吉布認為強橫一時的突騎施在中國人的外交陰謀下失敗,但也使中國人失去了一個抵抗大食人的堅固壁壘以至自己直面大食人[14]。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一再侵擾四鎮的突騎施並不總是對唐臣服[15],反而最終成為唐帝國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四鎮殲滅突騎施便不足為奇。然而貪心不足的屈底波並不滿足於此時的征服。誠如沙班所說,在713年和715年的戰役中,屈底波遠遠的進入了珍珠河地區,有時候遠達白水城,甚至深入拔汗那地[16]。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地區一直對唐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通過這些地區可以很容易的進入蔥嶺以東的四鎮,因而占有該地對保衛四鎮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際上,此前突騎施一再攻入四鎮劫掠便與其占領了該地區有關。據阿拉伯《年代記》載:屈底波於714年攻克疏勒侵入中國。雖然學者沙班及王小甫先生都否定了這一事實,但鑑於上述地理形勢,屈底波可能在進行一場小規模的奔襲戰是有可能的,只是瓦立德一世之死才使征服活動停了下來[17]。無論怎樣阿拉伯人在蔥嶺邊緣唐帝國的眼皮子底下放肆的活動已經嚴重的挑戰著唐在這裡歷時已久的霸權。
《資治通鑑》卷211開元三年(715)條載:「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篙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孝篙自攝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徐級,阿了達與數騎逃人山谷。孝篙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羈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這就是發生在715年著名的拔汗那戰役,監察御史張孝篙率兵打敗了吐蕃與大食共立的拔汗那阿了達,威振西域。『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這無疑是唐對吐蕃、大食等國在蔥嶺邊遠地區的挑釁所做出的強硬的反擊,只不過與唐作戰的只是吐蕃支持下的阿了達而不包括阿拉伯兵,當然也談不上大食等遣使請降[18]。事實上,大食兵在唐軍到達此地時的兩個多月前[19]像一個謎一樣已經撤走了。但無疑,這場規模並不小的戰役不僅達到了將吐蕃人驅逐出河中地區的目的,同時也似乎震撼了阿拉伯人,使其遣使通好[20]。
關於大食人突然撤兵的事件至今都令人不解,我們都知道驍勇善戰的屈底波就是這個時候被部下刺殺,據說是因為反抗哈里發蘇利漫在拔汗那被部下殺死。蘇利漫對這些遠征軍下的第一道命令即是讓他們回末祿去,並在那裡把它們都遣散了[21]。由於史料的局限,這期間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以推斷,其必然與大食內部各派權力鬥爭有關,同時似乎也與其對中國人的外交政策有關,我們知道此時的阿拉伯政府一直對唐遣使不斷,其中713年,阿拉伯呼羅珊總督屈底波的一位特使來到中國,代表屈底波向中國皇帝傲慢的宣布,如果中國皇帝不向他進貢,他的鐵騎絕不會離開中國,而中國皇帝威脅他說:你已看到我偉大的帝國,回去告訴你們的指揮官,最好在我對自己的軍隊下令打敗你們之前撤退。但兩國最後達成了和解[22]。也就是說,兩國都有意在避免戰爭。事實上,大食人應該知道他們的實力並沒有達觀到可以觸怒另一個龐大帝國而去征服一片與那個帝國有著親密關係已久的土地。任何一種同盟都可能對其在中亞的霸權形成巨大的威脅。不幸的是屈底波並不太在意這一道理,這個被勝利沖昏頭腦的將軍似乎對踏上中國這片富饒的領土更加感興趣[23],但事實證明聰明的阿拉伯上層最終並沒有這樣做。這就使屈底波的死多少有些罪有應得。不過,他的死無疑使唐阿兩大帝國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又推遲了幾十年。
正如巴托爾德所說的那樣大食的霸權註定在這些地區建不起來,他們對這一地區的占領還需足足等上一個世紀[24]。然而正當阿拉伯人退出珍珠河以北和十姓可汗故地的時候,吐蕃人的勢力卻乘機深入到該地區。拔汗那一役,唐軍又一次將吐蕃人驅逐出蔥嶺以北,此後唐蕃之間的爭奪便轉移在蔥嶺以南諸地。需要說明的是終唐一朝,吐蕃人的威脅遠勝於在更遠的西方活動的大食人,因而驅逐吐蕃人牢牢控制蔥嶺邊緣地區以保四鎮便成為唐帝國在西部的首要任務。所以,因大食介入中亞以來所發生的西域諸國上書天可汗請擊大食事件唐一直未予答應,但對於受到吐蕃人攻擊的小國的呼救,唐一次次的不惜動用軍力。722年,繼拔汗那王請求擊吐蕃之後,唐又應小勃律王之請南破土蕃。總的來說,此後唐在蔥嶺以南對吐蕃的反攻,唐屢屢大獲全勝。天寶年間,日趨極盛的唐帝國展開了一場從劍南經青藏高原邊緣至蔥嶺以南的轟轟烈烈的全面反擊戰,使吐蕃人在唐的強大攻勢下全面收縮在青藏高原之上,一度停止了擴張。於是,唐與大食這對次要矛盾便上升為主要矛盾,且日益尖銳,怛羅斯之戰便是這種矛盾衝突的頂峰。
二、怛羅斯之戰的經過及唐軍慘敗的原因
公元747年,在安西都護三討小勃律未果之後,驍勇善戰的高仙芝進行了一場著名的遠征,在連雲堡大破吐蕃兵,斬首五千餘級。西方學者將此比作漢尼拔、拿破崙、蘇沃洛夫翻越阿爾卑斯山的遠征。此後又擊破薩比,播仙,天保九載應吐火羅葉護之請破偈師,因此而以「中國山嶺之王」而聞名西方[25]。同年又大破石國及突騎施。天寶十載,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偈師王,成為名副其實的常勝將軍。然而正是這個常勝將軍卻在怛羅斯大敗而歸,那麼究竟該戰役是怎麼打的呢?高仙芝又是因何而敗的呢?
由於戰役的結果是唐軍大敗而歸,後世史家對這樣一場重大戰役只是諱莫如深地記述了寥寥幾筆,造成今日研究的困難,但總算還有零星的史料使我們可以儘量復原其廬山真面目。
天寶十載(751)正月,高仙芝將石國王獻於朝廷,斬於闕下。石國王子逃到中亞諸國,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諸國皆怒,潛引大食慾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番漢三萬眾擊大食,深入七百餘里,至怛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眾叛,與大食夾擊唐軍,仙芝大敗,士卒傷亡略盡,所余才數千。」[26]《新唐書》列傳第60《哥舒高封》記載:「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與怛羅斯城,以直其冤。」《新唐書·西域傳》有一句:「攻怛羅斯城,敗仙芝軍」。綜上所說,我們似乎基本明白,戰役的起因是高仙芝伐石國,王子逃亡大食,企圖說服西域諸胡共引大食來攻四鎮,高仙芝聽說後率兵擊大食,以求先發制人,但葛羅祿臨陣倒戈,和大食夾擊唐軍,以至仙芝慘敗。但有三個問題歷來備受爭議。其一是唐阿雙方參戰人數多少的問題;其二是戰役雙方與怛羅斯城的關係。其三,戰後大食並沒有乘勝追擊的原因。
首先,我們來看人數的問題。《資治通鑑》卷216載「蕃漢兵三萬」;《舊唐書》卷109《李嗣業傳》載「兵二萬」;《通典》卷185《邊防》總序注載「七萬眾盡沒」。《資治通鑑考異》載「蕃漢兵六萬」;白壽彝先生認為《通典》著者杜佑之侄杜環親身參加這次戰役,所記之數可靠。姚士鰲先生認為七萬人可信,新舊唐書的兩萬人只是指唐安西漢軍[27]。也有人認為七萬人不確,如果加上大食的十幾萬人,怛羅斯城外小平原高地根本容不下這麼多人[28]。筆者認為依據杜環參戰而認為七萬說不太可靠,唐朝的兵團一般以萬人為單位,副將李嗣業所說兩萬人為安西漢軍比較可信,但拔汗那、葛羅祿人數難考,且參戰的華胡混和兵團並非都是高仙芝從安西首府帶出,而是高在遠征途中與所調拔汗那、葛羅祿匯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唐代雖說胡漢合同為一家,但仍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因此出征時蕃漢必分開各為陣營,且行軍打仗紀律嚴明,杜環很難知道除了漢兵以外的胡兵的人數。因此,他的七萬說,很可能正如陳大川,徐磊等人所說的那樣是被俘後從喜歡誇大戰功的大食人那裡聽來的。而阿拉伯人記載當時唐軍死傷五萬人[29],加之主帥伊步·穆斯林帶回撒馬爾罕的幾千俘虜,中國方面記載高仙芝只帶領幾千人逃回,這樣看來,唐軍參戰人數為《通鑑考異》的六萬人左右基本可信。大食方面的人數一般認為十五萬[30],甚至二十萬[31]。事實上,剛剛平叛完畢的阿拉伯正規軍不超過五萬人,加之阿拉伯帝國統治下的數萬突厥人,總共十萬人左右,應該不會有太大差錯。總之,阿拉伯混合軍團的人數遠勝於唐軍是肯定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新唐書》、《舊唐書》認為大食攻仙芝於怛羅斯城,《資治通鑑》認為是仙芝在該城與大食遇。這樣,我們就有必要知道在大戰前,究竟是誰占領著這座城,史書記載,怛城是石國的第二大據點,《新唐書·石國傳》「怛羅斯城,石國常分兵以鎮之。」這也是高仙芝與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32]。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大食很可能只是答應石國王子派兵駐守怛羅斯城,而且需要說明的是,在怛城不遠的撒馬爾罕,早已是大食兵聚集的據點。一直覬覦東進的阿拉伯人只是一直礙於唐對此的管轄而遲遲未動手[33],而此時唐與石國發生衝突,進駐怛城便成了難得的機會。但高仙芝並不知大食的意圖,而且我們知道唐在蔥嶺以西的屬國分散部署,一時很難集結,所以一旦大食來攻四鎮,很可能會像此前的突騎施一樣攻陷安西,為了阻止大食的東進,以攻為守,遠征大食對於深諳兵法的高仙芝來說似乎成為最佳手段,剛剛平定布哈拉和粟特的叛亂的穆斯林大軍匆匆南下,恰好與高仙芝大軍相遇在怛羅斯河,兩軍激戰五日,由於怛羅斯城守兵與南下穆斯林大軍合擊唐軍,兵力過分懸殊,及葛落祿軍臨陣倒戈,於是大食人和突厥人的聯軍在那裡徹底的打敗了中國人[34]。
關於阿軍為何沒有乘勝東進,大多數學者的觀點,認為怛戰阿軍勝的過於艱難,懾於唐軍強大的印象,不願東進挑起更大的戰爭。筆者認為上述原因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新興的阿巴斯王朝希望有效的梳理並不穩定的內政而奉行的暫時和平外交政策。實際上,此後,他們對中亞征服不斷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所向披靡的大食人從來都不會畏懼戰爭,因為真主會使他們戰勝一切人[35]。
如前所述,我們知道,唐軍的失敗與唐阿雙方的兵力懸殊脫不了干係,西方的學者基本持這一觀點[36]。但中國的許多學者總是對唐將高仙芝耿耿於懷.在攻打石國的過程中,世人對高仙芝多有指責,如高仙芝沒有信義,屠城,貪財。其實細細分析,這顯然有些強詞奪理。首先是說高仙芝沒有信義,根據是已經和石國國王和談,卻用偷襲。中國兵法歷來是兵不厭詐,李靖夜襲陰山,也是憑藉和談麻痹突厥人,而後一舉成功,世人多稱讚這一壯舉,為何高仙芝用這個辦法就是沒有信義?《資治通鑑》卷211開元三年(715)條記載「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明顯是高仙芝為了麻痹石國而用的謀略。然後是說高仙芝屠城,其實這是當時戰爭的常用手段,比如說開元三年之役,「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傳,自已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等八國皆遣使請降。」為何這個時候沒有「諸胡怒,連兵攻四鎮」呢?其實所謂的「諸胡怒,連兵攻四鎮」只不過是中亞河中地區的西域國家在阿拉伯的控制之下聯合進行的一次政治反攻活動,和高仙芝是不是屠城關係並不大。最後是說高仙芝貪財,這一點最為冤枉,兵法有云:「使貪使愚」。高仙芝正是完美的應用了這條兵法,所以他的軍隊才可以保持如此高的戰鬥力。大唐名將李靖擊滅突厥之後,被人彈劾說「治軍無法,突厥珍物,擄掠俱盡」,[37]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史書記載高仙芝「頗能散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38]可以明顯的看出他並不是一個很貪財的人。有學者還認為高仙芝就犯了兵家大忌,「深入胡地,後絕援兵」,後方補給不足[39]。其實,李靖當初率三千騎北擊突厥,又何嘗不是深入胡地,霍去病,追擊匈努幾千里,甚至到了貝加爾湖,又何來後援?但我認為這恰恰是高仙芝用兵的風格,而且這個距離,還不能算冒險,小勃律之戰的危險係數要比之高得多。這不過是喜歡紙上談兵的幼稚學者對失敗的將軍的無理取鬧。錯只錯在此役高戰敗而歸,倘若大勝,那麼他們的讚譽恐不亞於小勃律一役。此外,學者李方認為高仙芝「以其無藩臣禮」而討石國,屬於過激行為,造成怛戰大失人心,與阿拉伯軍隊相遇一觸即潰。其實,這只不過是討伐石國的一個細枝末節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石國的行為已經告訴我們,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石國開始使用這種尋找新的主人的方式來應對來自雙方的壓力。或者說,高仙芝伐石國不過是給阿拉伯人看罷了,他對石國人的懲罰越重越能震懾阿拉伯人。
此處我們還需對葛羅逯眾的臨陣倒戈作進一步的分析。關於倒戈的原因,史料全無,但怛邏斯之戰後葛邏祿人輕易崛起,控制了碎葉地區,這是眾所周知的。唐軍與多於自己一倍的真主的戰士們血戰五晝夜才開始奔潰而非一觸即潰,這不得不使我們推測在第五日的夜間,唐軍突然受到來自葛羅祿人和大食人的襲擊,如果是這樣,無疑是殺了唐軍一個措手不及,使其混亂而失去控制,因為直至當夜,高仙芝的損失也許並沒有那麼慘重,如果有機會使之重新恢復紀律,則完全有機會再戰[40],但困難恰恰是,當時在夜間,局面已經完全失控。《新唐書》卷138《李嗣業傳》記載,「會拔汗那眾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可見主帥與番將士卒已完全分散。
三、怛羅斯之戰的影響和戰後中亞的局勢
不管怎麼說,這場著名的戰役是以唐軍的失敗而告終,白壽彝先生認為,我們不必等到怛羅斯戰敗再看出唐帝國霸權的衰落,但中國的勢力也並非「遂絕於西方」[41]。不過事實卻更傾向於怛戰後的唐帝國國力仍處於上升階段。這個帝國終於花費了近一個世紀的心血在他極盛的時候將一直被視為最大對手的吐蕃人的勢力徹底趕出了中亞,當他們回頭發現阿拉伯人的勢力正在大大威脅他們的時候,富有遠見的高仙芝企圖將這些勢力像驅逐吐蕃人那樣趕出他們的領地,不幸的是,這唯一一次嘗試在葛邏祿人的倒戈下失敗了,儘管在同一年,唐軍在雲南和東北等戰役中也遭到了大的失敗,但這並不能說明唐在西域霸權的末落,事實上在唐高宗年間對吐蕃的幾次用兵損失不下於幾十萬,但那時的唐帝國同樣處於蒸蒸日上的階段。這次失敗和高宗年間的失敗一樣,都發生在邊境,不會影響整個帝國的根基,尤其對於這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財富、最高文明的大唐帝國來說並不算什麼,其龐大的積蓄不僅支持著它的日益腐敗奢靡的統治集團的揮霍,也支持者他的對外征伐,怛戰後的幾次大規模運兵無疑在證明這個帝國在西域的實力仍未根本動搖[42]。怛戰的失敗使阿拉伯人和葛邏祿人瓜分了帝國在碎葉十姓地區的霸權,正如西方學者格魯塞說的那樣,如果不是帝國內部的那場內亂,也許,不過幾年,他們就會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回他們的霸權[43],但是,隨後爆發的安史之亂卻使唐軍永遠的失去了這個機會,也正是這場來自帝國內部的持續八年的內戰,幾乎耗盡了這個強盛帝國的所有財富,衰落從那個時候才驟然開始。從廢墟中重建的那個帝國已不再是曾經的天可汗帝國,公元792年吐蕃人攻克了帝國在塔里木盆地的最後一個據點,漢人的軍隊在清以前的近八百年裡再也沒有踏上這片土地。
我們或許可以向教科書那樣把這場戰役看作是阻止阿拉伯人東進的一次雖敗猶榮的戰役,但我們也必須同意王三義的觀點:打響這場戰役並非是兩國上層的初衷,作為一場邊境守軍之間的衝突的事實是無可否認的[44]。但無疑,戰役的結果卻是阿拉伯上層最願意看到的。古代史上中國人唯一一次企圖跨過帕米爾去建立霸權的嘗試失敗了,儒家文明的保守性和厭戰性無法支持一個先進中國的對外征服,經張騫通西域以來直至中共建政兩千多年中國人的血本經營才使那裡成為中國領土的最西端,從而也使這場戰役成為中國疆域史上完全有必要記住的一戰。
至於由戰役的結果而引發的科技文明的傳播,其意義固然重要,但筆者認為造紙術完全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傳播。到公元750年左右,揚州、廣州已經是著名的世界性貿易港口,在廣州定居的大食和波斯人之多,以至於在公元758年的時候,他們竟發起動亂,洗劫了廣州城,然後駕船揚帆而去。海上貿易由於不那麼怕被劫掠,比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陸上貿易還要發達的多。造紙術完全可以以這種渠道傳播到阿拉伯。而且,認為造紙術的西傳緣於此次戰役,一直只是由西方的史學家提出[45],他們習慣用阿拉伯人從中國俘虜那裡學會了造紙術這樣的話來談起這件事,中國學者對此沒有做足夠的考證,我們只知道主帥伊步·穆斯林帶著幾千中國俘虜回到了撒馬爾罕,隨後這裡變成了阿拉伯人的造紙中心。筆者認為戰爭促進了這種技術的傳播不容置疑,但造紙術是在怛羅斯戰後才開始傳到撒馬爾罕的嗎?對此還需進一步研究探討。近些年,有學者已經考證,怛羅斯戰前撒馬爾罕的造紙術已從唐屬國拔汗那的首府浩罕和平而非搶劫式的傳入[46],但令人不解的是,怛羅斯戰役反倒被廣大「愛國史學家」塑造成了一座中華古文明向西方輸出的偉大里程碑,事實上,對於這樣一次被動的劫掠式的傳播,中國人付出了血的代價。
注釋:
[1]今哈薩克斯坦的塔拉茲。
[2]白壽彝:《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最早華文記錄》,《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11期。
[3]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77頁。
[4]參見張晶如:《淺析怛羅斯戰以及其影響》,《貴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5]李方:《怛羅斯之戰與唐朝西域政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王三義:《論怛羅斯戰役涉及阿拉伯與唐帝國關係的幾個問題》,《湛江海洋學報》2002年第2期。
[6]參見陳大川:《怛羅斯之戰與撒馬爾罕紙》,《中國造紙學報》2004年第2期。
[7]王若欽編《冊府元龜》卷991《外臣部》載:「以斯埃之子卑路斯走吐火羅,遣使來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之。」
[8]《新唐書》卷221《波斯傳》載:「是時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為都督。」
[9]參見王若欽編《冊府元龜》卷964《外臣部》。
[10]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98頁。
[11]《舊唐書》卷9《西域傳》載:「是時,大食強盛,西域康,石之類皆臣屬之。」
[12]白桂斯1987,第38頁,轉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32頁。
[13]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44頁。
[14]吉布1923,第85頁,轉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38頁。
[15]公元717年突騎施與吐蕃人聯兵攻四鎮,參見《新唐書》卷215《突騎施傳》。
[16]沙班1979,第70頁,轉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42頁。
[17]沙班1979,第70頁,轉引同上。
[18]參見李方:《怛羅斯之戰與唐朝西域政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19]大食人撤走是這年九月,而唐軍到達時已是十二月。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49頁。
[20]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附表《大事年表》:阿拉伯帝國次年譴使來唐。
[21]沙班1979,第75頁,轉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42頁。
[22][蘇丹」加法爾·卡拉爾·阿赫默德:《唐代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23]雅古比《歷史》記載過這樣一個說法:哈賈吉對他的兩個東方的大將喀斯木和屈底波許諾誰先踏上中國的領土就命誰做中國的總督。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43頁。
[24]《巴托爾德文集》卷1,第216頁,轉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63頁。
[25]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85頁。
[26]參見《資治通鑑》卷216《唐紀》32,玄宗天寶十二載五月。
[27]參見李方:《怛羅斯之戰與唐朝西域政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28]陳大川:《怛羅斯之戰與撒馬爾罕紙》,《中國造紙學報》2004年第2期。
[29]伊步·艾西爾:《全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14頁。
[30]參見伯揚:《中國人史綱》21《公元八世紀》,同心出版社,2005年。
[31]參見徐磊:《大唐驚變》第3章《悲情三人組》,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32]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90頁。
[33]蓋加運739年橫掃突厥餘孽時兵鋒直入怛羅斯城。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76頁。
[34]參見[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商務印刷出版社,1998年,第160頁;納忠:《阿拉伯通史》,商務印刷館,1997年,第186頁。
[35]塔巴里《年代記》卷二1195頁,轉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43頁。
[36][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商務印刷出版社,1998年,第160頁。
[37]《舊唐書》卷67《李靖傳》,中華書局,1986年。
[38]《新唐書》卷135《高仙芝傳》,中華書局,1986年。
[39]王三義:《論怛羅斯戰役涉及阿拉伯與唐帝國關係的幾個問題》,《湛江海洋學報》2002年第2期。
[40]《新唐書》卷138《李嗣業傳》載:「仙芝曰:『吾方收拾余盡,明日復戰』。」
[41]白壽彝:《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最早華文記錄》,《禹貢半月刊》1936年第5卷11期。
[42]713年封常清大破大勃律,陳千里擒殺背叛的突厥首領,中亞諸國最大規模的請求西擊阿拉伯帝國,出現在這時。參見王小甫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附表《大事年表》。
[43]參見[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商務印刷館,1998年,第160頁。
[44]王三義:《論怛羅斯戰役涉及阿拉伯與唐帝國關係的幾個問題》,《湛江海洋學報》2002年第2期。
[45]蓋茲威尼:《地理志》539頁「撒馬爾罕條目言:這裡生產『撤馬爾罕紙』」,除了中國造的,就再也看不到能與之相比的紙。《邦國道里志》作者講:它是由戰俘們從中國帶到撤馬爾罕的,當時,他們之中有懂得造紙術的人口,於是,這種技術被採用了。以後,它的產量增多,成了撒馬爾罕人的商品,遂從那裡轉輸到其他諸地。
[46]參見陳大川:《怛羅斯之戰與撒馬爾罕紙》,《中國造紙學報》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