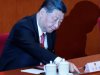來點思想
記者是一個卑鄙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楊繼繩
他是一名與眾不同的研究型記者:35年來除發表了數以千記的新聞作品外,還發表了數百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他以記者的敏銳撲捉問題,以學者的深度剖析問題的癥結;
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過毛澤東、周恩來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國新聞界挨批層次最高的記者,有兩屆中宣部長都曾經批評過他的文章。
他說,真相是威力強大的炸彈,它會將謊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燈塔,它會照亮前進的道路;真相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他說,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聖之間,沒有鴻溝、沒有高牆,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
他說,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與權力是硬幣的兩面,連在一起,掌握權力而不負責,就是歷史的罪人。

楊繼繩:高級記者、教授
楊繼繩,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理工學科,入新華社工作前後35年,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任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經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採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等職。
2015年12月,美國哈佛大學尼曼學會授予楊繼繩「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義獎」,稱楊「是一個榜樣,值得那些希望記錄人類黑暗而艱難鬥爭的人學習」。
隨後,因故未能出席頒獎禮,楊繼繩以文字的形式發表這篇答謝詞。
以下為答謝詞節選:
感謝評委會將2016年度的新聞良知與正義獎授給我。良知與正義這兩個詞的份量很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當作對我的激勵和鞭策。
我是很熱愛記者這個職業的。我在這個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據我的體驗和觀察,我是這樣評價記者這個職業的:
這是一個卑鄙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這是一個平庸的職業,迴避矛盾,不問是非,明哲保身,甘當權勢的喉舌;這是一個神聖的職業,胸懷天下,思慮千載,批評時政,監督政府,溝通社會,使媒體成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
這是一個淺薄的職業,只要能夠寫出通順的記敘文,不需要多少學識,不需要卓越的見解,聽話順從,就能如魚得水;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職業,記者不是專業學者,他需要從整體上研究社會、把握社會,無論有多麼淵博的學識、有多麼卓越的洞察力,在複雜多變的社會面前,都會感到學力不足,力不從心。
這是一個舒適而安全的職業,出入於宮闕樓台,行走於權力中樞,燈紅酒綠的招待會、歌舞昇平的慶典,訪大官,見要人,春風得意,風光無限。
如果用文章與權勢投桃報李,今日的書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窮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這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職業,且不談穿梭於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記者,就是在和平環境中,調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難萬險。一旦觸及到權勢集團的痛處,不測之禍從天而降。
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聖、是淺薄還是高深,在於從業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價值取向。真正的職業記者會選擇崇高、神聖、深刻、兇險,鄙視和遠離卑鄙、平庸、淺薄、舒適。
然而,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聖之間,沒有鴻溝、沒有高牆,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條黑色定律在記者職場十分盛行。要不被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無所畏懼,勇於獻身。
這也是我對新聞良知與正義的理解。
要當一名堅持良知與正義的記者是有風險的。我在給新聞專業學生講課時傳授了一個避險秘訣:「一無所求,二無所懼,自立於天地之間。」無所求,就是不求升官、發財;無所懼,就是檢點自己的行為,不留「辮子」被人抓;不依附權貴、靠自己的人格和專業獨立於世。有了這三條,風險就小多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很多堅持良知與正義的記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們報導真相,鞭撻邪惡,推動著中國社會前進。
昨日的新聞是今日的歷史。新聞和歷史的共同點就是信,即真實可信。信,是新聞和歷史的生命。
中國史家歷來重視史德:忠於史實,善惡必書,書必直言。以直書為己任,以曲筆為恥辱的史家,幾乎代有其人。為保持史家的節操,許多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真相有強大的穿透力,它可以衝破行政權力構築的銅牆鐵壁!
真相是威力強大的炸彈,它會將謊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燈塔,它會照亮前進的道路;真相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記者,就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
最後,讓我和大家一起,為記者職業祈願:願良知和正義的陽光照亮千萬個記者、作家的書桌!願更多的作品喚醒人類的良知,讓正義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下文是《南風窗》高級記者郭宇寬對話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的摘錄。看得見歷史的殘酷和現實的進步,以及現實的不足。
說真話,做真人
郭:這些年來你是怎麼適應記者生涯的種種情況,並且有後來的成就啊?
楊:我把當記者的這三十幾年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時候比較年輕,以見報率為榮,發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緊跟形勢跑,拼命寫,發表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幫」後,我把這個時期的稿子盤點了一下,發現90%的都應該付之一炬。能留下來的稿子只有兩篇,一是1972年與馬傑合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這兩篇是根據老百姓的呼聲寫的。十年的教訓使我學會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我雖然早就認識,但真正理解它還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價。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後的十年。新聞事業出現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雖然不能完全講真話,但可以不講假話。
第三個階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職稱評完了,到頂了,沒什麼後顧之憂,連那些不真不假的應景之作也很少寫了。這十年我儘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了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歷史曾讓記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價
郭:很多人都就這樣過來了,你為什麼會是不一樣的一個?
楊:這個過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個否定自己的過程,特別是否定那些被別人看成是自己成績的東西。在我說的第一個十年,曾經有一年上過《人民日報》的12個頭條,姚文元講話,我們就跑到工廠里,找幾個工人談學習講話精神深受鼓舞的體會,回來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講話就更不要說了,這叫什麼新聞記者呀?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
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而黨性就是階級性,就是你的立場,如果你追求客觀就會被批評是站錯了立場,而新聞也被當工具來利用。我還有一個朋友他報導了焦裕祿,說焦裕祿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毛選」一本是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後來劉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書是「毛選」,再後來劉少奇平反了,又成了兩本書。
那個時候當記者付出的人格代價太沉重了。
很少懷疑,不敢懷疑
郭:那個時代,是我們國家遭受災難的年代,你在當時做那些歌頌報導的時候,有沒有懷疑過?
楊:很少懷疑,或者說覺得有問題也不敢往深入懷疑,說起來你會覺得奇怪,我父親就是給「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而我當年還歌頌大躍進呢。
我在後來一篇文章里寫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團委辦「五四」青年節壁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我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