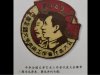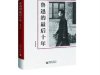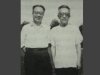常地聽到這樣的開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他走到大街上隨處浸淫在領導人卡通式的微笑以及「共產黨好」這樣的宣傳標語裡;甚至早在小學,連能無差錯地寫下「政治」二字都尚存在困難的幼童,就已在少先隊的旗幟下完成了他們人生第一次莊嚴的政治表態:「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固然,學理上我們不難區分馬克思、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然而對於一般民眾,尤其是初涉世事的少年來說,想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在實踐上海納百川的概念族進行界定,談何容易!在以理論的姿態介入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前,這套貫穿於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早已在先塑造了生活於其中的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
第一章所談到的是一些零星概念及「哲學真理」的習得,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固然可以被視為我對馬克思主義管窺地認知的開始;但他們卻並不是塑造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感情的最重要因素。我自認為是一個有著強烈的「自由主義衝動」的人,用白話說就是「天生反骨」:我慣於挑戰權威、儘管這些權威大部分在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又樂於質疑傳統,然而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傳統事實上是有被堅持的價值的。也正是因為這種被我媽批評為「懷疑一切」的「缺點」,我的人生旅程上多了不少本可以避免的坎坷。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撞南牆不回頭」的人,怎能不對這一套籠罩整個社會生活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有叛逆之心呢?
寫到這裡,我兩次用了「馬克思主義」實踐這個表達。事實上,在下筆之前,我也對「實踐」這個詞斟酌再三,為了能恰如其分地指稱這個對象,而又不「劇透」接下來的討論,我才權衡以為以加引號的方式表達這個意思。而接下來我想要談的,也正是章前題記中哈維爾的著名意象所象徵的,就是這個「馬克思主義」實踐,事實上其本質業已異化為了一套「後極權主義」的儀式。
所謂「後極權主義」,是哈維爾對1970年代布拉格之春之後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社會氣氛的描述。其要旨在於,作為一種激進的社會理想的共產主義的政治產物的極權主義已被歷史和現實的銳利磨去了鋒芒,無論是執政的黨政精英還是一般的普通民眾,共產主義所要求的那套意識形態上的激情與夢想早已不復存在。然而,威權體製作為共產主義時代的政治遺產被保存了下來,「去共產主義化」的共產黨官僚精英仍然壟斷著國家政權。這時,他們需要一套新的社會意識形態來支撐他們的統治合法性,然而,如果傳統的共產主義大旗已經褪色,新的支持者又從哪裡來尋找呢?於是,一方面,整個社會轉向消費主義,為了物質實惠而放棄了道德和精神尊嚴;另一方面,社會也瀰漫著政治冷漠,對政治現狀採取消極服從的策略。而這種個人的消極服從的社會形式是什麼呢?就是一套象徵著服從的社會儀式。而這套社會儀式從何而來呢?已經被剝去內核的共產主義話語體系就是一個當仁不讓的選項。
這才有了章前題記的那個絕妙意象:一個普通的水果店老闆漠然地在櫥窗上貼上共產主義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這句簡單的標語裡,革命激情萬丈的共產主義與政治冷漠泛濫的後極權主義跨越時空地交織在了一起。字面上看起來,一切都沒變;紙背後看過去,什麼都變了——當然,也有更聰明的修辭家,還可以發明「XX化」「XX特色」這樣異想天開的過渡句,把這一改弦更張添汁抹粉為「理論創新」。美其名曰,這等專事調和的「和事佬」們的確可以在中學作文的意義上說是「辯證法」的化身啊!
水果店老闆的標語,只是這個繁複的儀式符號體系中的一個原子罷了。當他在貼上這句標語的時候,他從來未有對標語的內容進行過嚴肅的思考,而只是想表達:「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該作什麼,是守本分的。我是個靠得住的人,無可挑剔。我很聽話,所以該過上平安日子。」而捫心自問,當我們從小就每天帶上紅領巾宣誓自己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時候,我們有反思過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麼?當我們在爭相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又有否追問過究竟何謂民主、自由,十二個要素是否相容,又是否完備?而當我們在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所謂「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有可否花一剎那考問民主何以集中?集中何以民主?在這些微小的時刻,我們都是這個無意識地貼著標語的水果店老闆;而在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若隱若現存在著這樣標語的身影。這些點點滴滴的標語作為原子,構成的是整個社會的一套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謊言的體系。生活在這一套謊言的意識形態之下,反抗的「自由主義衝動」不過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罷了;而磨滅了這種傾向,從而對謊言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才是一種令人悲哀的人性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