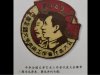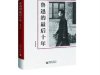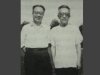從「論猶太人問題」開始,在方老師兩學期的課程內,我又陸續閱讀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德意志意識形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等經典核心文本,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形態有了一個入門性的了解。這時我對他的感情已經完全顛覆了,這位可愛的德國人已然成為了一個未來可以繼續挖掘的精神寶庫。然而,彼時我的興趣轉向了邏輯學和分析哲學,因此對馬克思的閱讀也就此暫緩了將近兩年。
四
每當世界上出現普遍性的社會危機的時候,人們總會想起馬克思。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建黨立國的理論基礎的中國是如此,對其毀譽不一的西方也一樣。這是這位畢生致力於對現代社會進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當代影響的表徵。但是,我認為,馬克思不需要以這樣的方式彰顯其存在!這樣的做法,無論動機如何,只會敗壞他的聲譽!——聶錦芳:「馬克思不需要以這樣的方式彰顯其當代存在!」,2020年
2020年,香港反送中的如火如荼、國際局勢的風雲詭譎,尤其是疫情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巨大衝擊,無不讓我感到有重返對政治與社會的思考的必要。於是,一方面,我想更多地了解現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討論,二方面也想再拿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過與二位先賢的交流重塑我對人類社會的認識框架。而由於學校在前一領域內的課程較少,因此我著重加強了對馬克思的繼續了解。
因此,在疫情過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修了方博老師的「馬克思國家理論研究」課程和仰海峰老師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專題」課程。從後一課程中,我感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極強的創新能力,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論上都大受啟發;而前一課程中,我們詳細地閱讀了從早期《萊茵報》時期的「理性國家觀」,經《形態》「成熟時期」的「階級決定論」,再到《法蘭西內戰》《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國家更具獨立性色彩的後期理論,認識了馬克思思想的複雜性和多變性。
本學期,我選修了聶錦芳老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希望能對後續的學習有一個歷史線索上的鋪墊,我認為前大半學期的學習也基本達到了我的預期。一方面,聶老師文獻學知識的補充(最典型如「巴黎手稿」部分的介紹)填補了過去我的很多知識空白,而這部分知識是很難通過自學進行了解的;另一方面,其他哲學系課程並不太關注《手稿》以前的馬克思思想發展,而聶老師幫助我們搭建了這一線索,並強調了馬克思與其前輩思想家及歐洲思想傳統之間的關係,這個部分對我也很有幫助。
二十多年與這位德國智者一路走來,這就是我的「馬克思思想接受史」。放眼前望,未來我也有可能專事與他相關的研究,只不過具體的研究計劃及是否要決心走研究之路都還尚未決定。然而,至少我現在完全認同,這位思想家是非常有研究的必要的,這至少有以下的幾點理由:
其一,馬克思思想具有當代價值。這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我想正像本章題記里聶老師說的那樣,每當世界上出現普遍性的社會危機的時刻,人們總會想到馬克思。這正是因為,馬克思一生所致力於刻畫的資本仍然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要素,而後來的思考者也都未能完全超越他的資本分析框架。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尚未過時,馬克思主義就仍有他的生命力。
其二,馬克思思想具有開放性。這同樣是老生常談。一方面,馬克思並非學院派哲學家,不同時期的思想間本就可能存在很大不同,而這也給了後世讀者以開放性解讀的空間;另一方面,馬克思思想也有不完整性。例如他並不關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掌握國家的具體方式(政治學,後來被米利班德《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等著作所填補空白)、對未來理想社會人類的生活狀態的描述也非常簡略,需要更多的理論生發。
其三,馬克思思想在當代處境尷尬。如前所述,在淪為了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衣後,就像年輕的我那樣,社會公眾對於馬克思必會產生多樣而繁雜的誤解。如果能夠在宣傳上消除這種誤解,為馬克思主義正本清源,揭示「偽馬克思主義」的醜陋嘴臉,這也未免不是於對馬克思思想傳播的有意義的工作。
最後,讓我再次用余華文章的精彩結尾來表達我與馬克思的這段糾葛的情感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