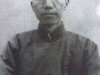楊絳說張愛玲「一臉花生米」已不可考,然而她說這話時,是否已成「漏雨蒼苔」?自己描述的這四個字,活脫脫中國文人一張臉,「蒼苔」如滿臉皺紋,「漏雨」似狼狽不堪,實在絕妙,但是溫飽與尊嚴皆失的中國大眾哪裡還欣賞得了?
況且2016年老太太105歲辭世,長壽得驚人,「長壽」在苦難歲月中乃是一種富貴了,尋常百姓簡直無法逼視。所以「盛世」里弄出這場菁英與大眾的誤會,倒也經典得很,是文化爭議還是政治歧見,誰說得清?不過它預示了在體制與民間博弈之外,文人與市井還需要磨合,則是肯定的。中國的言論環境,已經無法討論政治話題,那麼文化話題呢?因為更複雜更彎彎繞,習政權也不會懂,恐怕也是一律禁止的。這讓我想起前幾年一個「文人精明」的討論,蠻艱深而又有意義的辯論,早已像一縷青煙消失得無影無蹤。
張愛玲楊絳撕X簡史|傳遞閱讀的樂趣
一、文人精明
2016年楊絳105歲仙逝,各大媒體和社交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悼念,有人譏曰「夾雜招數不清的『雞湯文』」,最刺目是官方罕見褒揚,民間則褒貶爭辯甚激烈。楊絳九十二歲開始「小清新」寫《我們仨》,以意識流手法描摹「客棧」、「古驛道」,感嘆「枯藤殘柳,蕭蕭落葉,漏雨蒼苔」,直引得國人無比驚嘆,贊為「淡泊功利的人格典範」。然而有人說,中國人活得像豬一樣的事實,在老人筆下成了「夢境的邈遠迷離」;也有人評定:這一代知識分子很難拔得太高,幻想中做貴族,動機善良,行為盲目,中國走了六十年邪路,也有他們一份。這次風波無意間流露社會對所謂「文人」的集體無意識,不議一下都可惜。
早在1998年錢鍾書走的時候,已起毀譽論戰。當時的焦點很奇怪,不是人格而是錢的學問。有人引述了李澤厚的評論:
「我問過推崇他的人,錢鍾書到底提出了什麼東西?解決了什麼問題?有長久價值的。大家大都講不出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好像這個『杯子』,他可以講出許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義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國、外國怎麼講,那是很多。不過這個工作,到電腦出來,就可以代替,電腦記得更全。所以博聞強記就不能成為一種標準。他讀了那麼多書,卻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李澤厚有無此評價,我很懷疑。學問本來是無功利的,談什麼「永照千古」?據說余英時藉以賽亞•伯林的「狐狸型」和「刺蝟型」思想家分類方式,界定錢是狐狸型學者,即淹博淵通、無所不知,刺蝟型則獨掌一技、思精體大,前者缺乏系統,後者缺乏細節,各有短長;余認為錢對思想體系沒興趣。
當時最激烈的評價,來自劉曉波。他說「錢學」已成一門新學問,而且江澤民的中共第三代對「錢老」都很尊敬,乃是重量級統戰對象,但是他認為「錢鍾書的學問沒有獨創性」,一部《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注經陳調。然後,劉曉波第一次質疑錢楊的生存之道謂之「沉默」,觸及到文人在專制下的「人格」,也是知識界無法迴避的題中應有之義。
1998年錢鍾書去世之際,余英時寫了《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他認為錢鍾書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錢鍾書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後兩句為:筋力新來樓懶上,漫言高處不勝寒,余英時認為這是錢的「詠懷詩」。2007年余英時再次評錢:
「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在事變中怎麼樣適應,而同時能夠保持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原有的原則,不會做出很不好看的樣子,或者像馮友蘭那樣一再罵自己,他都沒有做過。這就是他能夠繼續不斷的學問,繼續做學問。只要你沒有別的任務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筆記。」
余對錢,保持了「傳統文人」的雅量,或曰「同情的了解」。這麼說,是因為余英時不僅在乎讀書人守住「文化的操節」,以詮釋晚年陳寅恪,展示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的承偌;而且,他也毫不客氣地批判四九後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新「傳統」——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晗,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皆為陳寅恪所謂「改衰翁為奼女」的顯例;過去人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有「敢犯龍顏」之風骨,後來的資料卻顯示,馬寅初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而較早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吭氣。
這些事實,都顯示「文人」乃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一個複雜、艱深的課題,難在究竟以何種標準定位他們:「舊式文人」,還是「知識分子」?若以後者論,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幾無合格者耶?
當年同儕如楊憲益回憶錢鍾書認為,其實鍾書兄是個書呆子,整天沉醉於書堆里,置一切於不顧。當時並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其實我知道他是個很真誠直率,很關心別人的知識分子」,楊也指出,錢鍾書雖然最後一二十年間被大家吹捧得紅得發紫,而且引起許多年輕人羨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許多不公平的評論,好像他學問太大,是個怪物:
「最近他去世後,還有人編造各種離奇故事,不說他被人欺負,反而倒咬一口,說他行兇打人等等。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死後還要給人作為話柄,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替錢楊辯護:
「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國文人學術上的私傳統(文人們自己玩),他的這些學術筆記並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學術作品,他沒有這個興趣,他只是自娛自樂,沉浸在讀書的樂趣中,在那樣的知識海洋里遨遊,不拍出點水花來都難……錢楊兩位所處的時代,在其一生事業最鼎盛的時期……超過30年,那是個動輒得咎的年代,以他們兩位在學界的地位,能夠沒有害過人,不說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說他們犬儒也好,說他們懦弱也罷,都是苛刻的。他們在政治上是圓滑的,但如果沒有害人僅僅為了自保有什麼錯呢?至少不應該作為公共批評的事實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