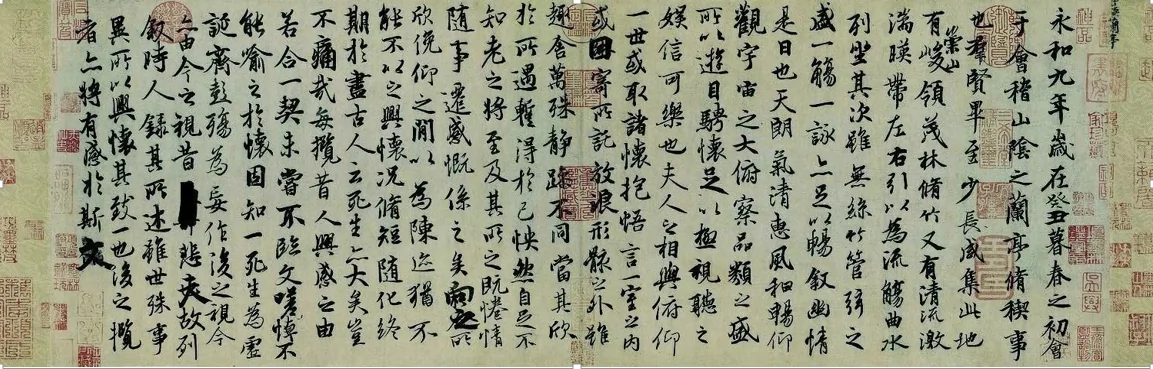![]()
近日和不止一位在大陸的青年學人談到安身、立命和立名的問題。
我之所以和他們由問題之交進而提到安身、立命、立名問題,是因為文字之交多了,儘管不曾謀面,卻也多了幾分人之間的友情,他們都是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因而交談也就關切到這些涉及學人人生的根本問題。
我並不知道他們各自的氣質、處境及對自己的設計。但是我知道,為人一場可以有多種形式的演繹。對於傳統社會的讀書人來說,子牙、子房、諸葛是一種,竹林七賢亦是一種,出仕、隱居、瀟灑人生還是憂國憂民,先天下之憂而憂,根據個人的氣質及志向,乃至後天的條件,各有其志,也各有其路,實實地不可勉強。
然而,這一切對於現代社會來說,卻和傳統社會有所不同,現代社會,因為它沿用的一切都是西方基督教社會的結構,不過是一個世俗化的教會社會,所以它用政治和經濟把人牢牢地禁錮在社會這艘船上,跳船和下船不可能,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船上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而這個不同導致了你在選擇道路的時候更要對自己所要面對的形勢、未來有較為充分並且現實的估計。為此,所謂現代社會對人的生命歷程的風險性或許說更大。這大約也是現代社會中知識人因為個人及社會的不協和而自殺的更多的原因。為此在和青年學人的交往中,隨文字交往我希望能夠談點關於安身、立命及立名的看法,並且希望在這些方面對他們有所助益。當然也只是參考及因勢利導而已。
1.關於追求知識與社會存在及學位
對於也走向我這條道路的年輕人的實際性的幫助,由於我走的是純文人的道路,,在這方面的能力日益萎縮,因此我實實地感到慚愧。實際上我也是希望自己的這種能力萎縮,因為過去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尤其是七十年代,我在北京交友三教九流,確實是有些能力,但是自我決心從事思想文字後,意識到這不僅浪費自己的時間而且腐蝕性情的敏銳,因此自覺地封閉自己,不再擴展自己的交往。此外,自然就是凡是研究學問及思想的人,恃才傲物是其必然,所以這些年來我不僅主觀上自覺地尋求孤獨,而且客觀上追求的陽春白雪也同樣導致和者必寡。
我這樣的人,倘若是生活在正常社會中,在年輕時,還在成長的時候即可以進入到學院中,待到他們發現你的孤傲不群,你已經有了自己的根基。但是生在亂世,封閉的時代,則註定了你的不入世。而這就註定了我現在的情況。我自知,必須徹底地犧牲「混」世,才有可能踏踏實實地去做一些不是自欺欺人的基本的文字及思想修養和工作。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孤獨」「困苦」。
古來聖賢皆寂寞,我非聖賢,追求卻也讓我體會到寂寞。
然而,人的存在組成的世界是很「勢力」的世界,你不去拉拉扯扯地混世,沒有勢力,沒有人間的權勢位置,你的實際運作的能力及影響就一定會減弱。所以時下我很慚愧,因為一方面自知對於和我交往的年輕人很難有實際的幫助,而另一方面,我卻又很是知道,這些有思想、有才華的年輕人可能遇到的困難,他們十分需要的幫助。
正是為此,對於走自學道路的年輕人,在進入這條道路的時候我首先就要提醒你們,現在社會的實際形勢註定了你們的路甚至可能會比我還要艱難。因為時下你所生存的環境已經完全不是傳統的中國社會環境,統治它的是來自西方基督教政教分離後的後基督教社會。世界已經是一個基督教社會的徹基質質化、世俗化社會。這種情況決定了它只承認那些在表面的物質及世俗存在基礎上的人。對此,我對很多年輕人說,雖然學位的問題一定要看穿,它不意味著什麼,但是因為它是一張門票,能夠拿到,就要儘快拿到。哪怕是合法地糊弄到。我所謂合法地糊弄,就是不要浪費時間,不要太認真對待它,儘可能快地敷衍它的標準,拿到它。然而你心裡卻一定要明白,這個學位並不意味著你很行。沒有它,當然也不意味著你不行,它只是一張必須的門票!因為時下在西方的影響下,在所謂正常的世俗社會中,你沒有學位就可說是幾乎被徹底地關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之外。
當然對此你們也不必絕望,因為人生、人世的情況永遠不會是絕對的。事在人為!而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可能性就更多了。這尤其是當你想到中國的未來:第一,那些個現在存在的大學及研究機構以後一定要重構,因為他們現在是被徹底地意識形態化、政治化的所謂知識機構。第二,現在那些有學位的人絕大多數是些缺乏能力的人,甚至廢柴。第三,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從來有民間存在的第三類文人的重要地位及作用。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從來不是一個等級社會,它和西方不一樣,社會對這類文人學士永遠是另眼相看。因此在華人社會,只要努力,發展起來,就會有更多的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它遠比在西方社會的可能性要大。為此,對青年人來說,如果有志做一些能放的住、對得起生命及人生的事情,就要立長志,在一個方向上努力,有所長,有別人所不能,才是立住自己的唯一可行之路。
2.談張愛玲的「成名要早」及現代社會的「名」
安身、立命與立名,這問題對我們作為人而生存一場的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根本性的問題。它涉及人為何而活,如何而活,活著有什麼意義。五十年反叛的經歷讓我對於這個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於很多以前覺得彷徨模糊的問題也有了較為清晰的辨識,至少是感覺到了它們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是一種徹底的西方來的極端化了的文化。我對此有著切膚的體會。如前所述,現在我認識到了,它不過是一種徹底地世俗化、物質化了基督教文化。除了沒了神、沒了上帝,用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教會的位置外,沒有任何創新。它把人從過去置於上帝的主宰下而變成在世俗的領袖的主宰下,從教義、教條變成觀念、黨控,人立的所謂憲政之下。人在這種世俗化的西方思想底下是孤立的個體,而非一種和宇宙間生命及自然有著不可分割的天然聯繫的內容。
在基督教文化中,過去它在上帝的屬下,上帝主宰它的一切,他只需信仰、膜拜,關注此生他自己的生活,因為他人——父母、子女都自有上帝看護,而在所謂現代社會中,即在政教分離後的市民社會,他是世俗世界的個體,毋須受信仰及倫理的束縛,則成了只需關注此生的物與欲的生活。所以,被拋入到現代社會的極端化的產物,黨國社會中的我,在二十歲時雖然徹底地從黨國中反叛出來,但是直接進入的卻已經是西化影響下的世俗化個體領域,而並沒有立即有意識地重新思索更為根本的人的存在問題。因此我直接進入的是歐洲政教分離後發生的所謂浪漫主義(romantic)潮流。這個romantic,我曾經提到,它所具有的個人取代上帝的那種膨脹及衝動,翻譯成「濫漫主義」更為貼切。它使我把生命看成是以個人、物質及欲望為基礎的人的生命、人的衝動的實現。所以我那時,以及其後很長一段時期極為欣賞的是法國著名小說家司湯達為自己寫下的墓志銘:
「生活過,戀愛過,寫作過。」。
——這句話可說是集中反映了近代西方對於生命和人之欲之密切關聯的理解,可說是在政教分離、世俗化的十九世紀的基督教社會中,個人取代各種宗教曾經占據的位置的濫漫主義的銘言。它或多或少地主宰、影響了我那一代人中有些個性及思想的人。
但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人強調得是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名之為名,在中國人來說並非直接、完全地和人之欲望相關,它更多地是和倫理相關,和家族的血脈傳襲相關,即和生命的聯繫有關,和歷史的延續有關。
在這個意義上名之為名和生命之更為根本的意義相連,而非表面的欲望及物質。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名實》說:「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這代表了我們中國文化傳統中對於生在社會中的人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看法。他參透了我們中國人在我們對於天地人的關係,對人的認識的看法。
然而,這種看法,這個傳統在最近半個多世紀的西化席捲下,一切都變了。張愛玲的話大約很有代表性,她反其道而言之,提出「成名要早」。這不僅影響了一兩代人,而且甚至是很多並不知道張愛玲的這句話的人也是以此為目標。例如我的同代的很多從事文字的乃至政治的人,他們從步入人生,從在中國社會開始開放的七九年步入與世界的聯繫起,甚至直到今天,到西方媒體上曝光,獵取聲名是他們活著,以及從事文學及知識活動的中心目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張愛玲的說法感到困惑,卻不知如何認識。現在我清楚了,這是典型的世俗化、物質化的基督教社會,後基督教社會的世俗文化現象。因為他們沒了信仰,沒了形上學的價值及精神的前提,自然「名」、「利」,就是「此生」唯一重要的事情了。因為「此生」是孤立的「個體」的存在,它已經沒有傳統的那些生和生之聯繫以及伴隨它的神聖及顧忌。
為此它也讓我明白了,後基督教社會,基督教社會政教分離後的世俗化、物質化決定了這個沒了宗教前提、形上學前提的社會,一定是一個世俗觀念化的社會,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即各類意識形態無處不在,而這就註定了「名」在這個所謂現代社會中,後基督教社會中的位置及作用,決定了人們利用意識形態獵取名利的特性。所以和所謂開放同時而來的,從西單民主牆、朦朧詩人們步入人生開始就具有的到西方媒體中混名、甚至騙名,利用各種可能行銷自己的傾向,如今依然越演越烈也就毫不奇怪了。
3.從著書忌早談中國傳統的「名」
和張愛玲的成名要早成為對立的是齊如山先生所強調的,來自他父親身教和言教的「著書忌早、處事忌巧」的銘言。
「著書忌早、處事忌巧」,這是典型的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做人行事的銘言。我想,年輕的時候——沉浸於全盤西化時期,即七十年代,我是不會理解到這句話的深刻的。時過五十年,由於認識到文化的不可通約性、多元性,我知道,同一個「名」字,由於出自不同文化,它所意味著的意義不同、內容不同。文化人的「名」涉及的不僅是具體的學問如何,而且涉及最根本的對於「人生」的認知和信仰。
「著書忌早」和「成名要早」對名的看法的根本不同在於,它重的不是名為個人帶來的利,而是名對於一個人的生命所意味著的意義。由於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個個人的生命既和在西方社會中曾經是上帝的奴僕的個人不同,也和現在社會中的孤立的個人不同,它是代代相連的生命,是天地人中永存的生命聯繫及存在的生命。對於這個生命,人當然用人的有限的感知及認識無法企及,然而,中國人卻確實相信它存在,於是在中國文化精神中用看不見、摸不著的「氣」來歸類它。它認為,這個生命參的是寓於尋常之中,塞與天之間的氣,它「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名非一世、一人之所有物,而要經過百代千秋、前生後世的檢驗,匆忙浪得其名、名實不副、則不僅「欺人」而且「自欺」。因為它不僅和你活著的時候有聯繫及影響,而且還和你所不知道的身後,不僅和你,還與直接和你的生物存在聯繫的、你愛的子女,及後世的一切可能和你相關的人有聯繫。你能徹底地騙嗎?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你騙得了現世,騙不了後世。而於此,中國人還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對於急功近利對人的危害的警告、告誡及教導存在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其所圍繞的都是這個道理。而由此,你就會看到,和西方文化不同,中國人是最重「個人」的「責」與「任」的民族!與此相對,基督教文化要求人們首要的是服從上帝;現世的西方,則把個人推到了無限的絕對中心,最高的位置;而現實的中國的所謂知識精英們,既沒有了中國傳統的美德,也沒有把「名」服從於「上帝」,他們只有個人的物慾而沒有個性,是因為他們是受世俗化的黨國教育而來。
由此,我們當然也能夠看到,張愛玲的「成名要早」,實在是五四後全盤西化的產物,是反傳統,反中國文化之道而行之的產物。它的影響對中國人的文人精神是顛覆性的,可說是西來而最終由黨國推向極端的文化革命潮流中的外一篇。
為此,我極端厭惡張愛玲的「成名要早」的說法,而牢記齊如山現實的「著書忌早、處事忌巧」的叮囑。我以為,治學、立命、立名,不能夠急功近利,要慢、要逐漸,要紮實。也正是基於這點。為此,我希望對每一個年輕、能夠讀書的人說:切切離現實政治要遠!因為讀書治學需要一個漫長的修養砥礪自己的過程!
我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是否想過這些問題,是否黎明即起,是否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個設計。我是已經很認真地在考慮來向我求教,和我討論的年輕人,如何做,能夠點點滴滴、一步一個腳印的治學、立命、立名。而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如果你願意走向我這條路,那現在就應該考慮如何在現實的學界、思想領域起步、邁步的問題,即雖然不是要早日成名,但是要及早提出要研究的問題,以及研究的方向、思想傾向。因為我的經驗告訴我,後來者、後發制人會有很多不利因素,事倍功半。即如齊如山,他對於中國文化及京劇問題的提出,是在上個世紀的一〇年前後,此後走了半個多世紀。
「做事針針見血、一步一個腳印」
一九七〇年冬季我登泰山,山腳下的一塊不大的刻石銘刻了這十二個字,它影響我一生。我以為,它涉及治學、立命、立名。而這三點則要求你絕對不能夠急功近利,要慢、要逐漸、紮實。
積我七〇年到今天將近五十年的經驗,我看到,成名要早——那個「名」常常是虛的,名不副實,而這就決定了你一定會付出人生的代價,補交學費,甚至還可能有更壞的結果,它讓你由於年輕無知,誤入歧途,而在此後無法回到正途。而如果是「欺世盜名」,那在思想史、學術史留下的結果一定是更大的悲劇。
不是成名要早,而是針針見血;青年人要切切牢記著書忌早,一定要步步紮實。
這是積我五十年反叛,五十年追求的教訓。
2018.6.德國·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