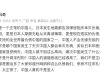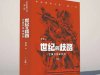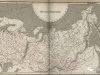次世界大戰爆發,「立刻就證明了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國際主義簡直就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而在1918年的戰後和會上,『民族原則』又再度大獲全勝。」【8】列寧顯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意識到必須及時調整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他發表於該年的《論民族自決權》一文,提出了遠比羅莎·盧森堡更為激進的「民族主義」主張,認為獨立的民族國家造成了能夠最充分發展商品生產,能夠最自由、廣泛、迅速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因此,「民族自決權」的實質,「除了政治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能有什麼別的意義。」【9】不僅如此,列寧還進一步認為,承認「民族自決權」就是承認民族的「分離權」,他為此規定了俄國無產階級應該完成的雙重任務:
「一方面要反對一切民族主義,首先要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不僅要一般地承認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認建立國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認民族自決權,民族分離權;另一方面,正是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民族主義勝利地進行鬥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組織的統一,使它們不顧資產階級的民族隔絕的傾向而緊密地融合為一個國際整體。」【10】
列寧的上述言論是試圖在堅持國際主義的前提下將日趨流行的民族主義話語引入到馬克思主義話語系統,這是國際形勢發展迫使他作出的話語策略調整。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第二國際」的解體,歐洲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路線宣告破產。羅莎·盧森堡作為一個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在與列寧發生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爭論時,還沉醉在國際主義的神話中,當她目睹戰爭爆發後歐洲參戰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紛紛選擇支持本國政府的戰爭政策時,她體驗到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絕望:「這是第一次在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需要同各國人民自由和民族存在的利益之間出現鴻溝,這是我們第一次發現各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迫切要求操各種不同語言的無產者互相殘殺和互相滅絕。以前我們一直確信,各民族的利益同無產者的階級利益是和諧一致的,是同一的,互相不可能發生對立。這曾經是我們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是我們在人民群眾中進行鼓動的靈魂。……我們面臨著國際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問題。」【11】如果以盧森堡的觀點來看列寧的「民族自決」論,後者似乎完全背離了馬克思所確立的國際主義路線,不僅贊成反對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而且贊成所有弱小民族均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力和建國的權力。但是,實際上列寧並沒有從國際主義路線上後退半步,他所提倡的民族自決的前提是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政治統治。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看法又有了重大變化,此時他不再認為「民族自決權」就是「民族分離權」,也不再認為蘇維埃統治下的各民族具有獨立建國的權利,他強調的是「共產國際的民族政策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派那樣,只限於空洞地、形式地、純粹宣言式的承認民族平等」,認為「只有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首先把無產階級、然後把全體勞動群眾聯合起來的蘇維埃制度,才能實際上給各民族以平等。」【12】共產國際規劃的新的國際主義路線,是動員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投身於保衛世界上第一個紅色政權的統一戰線。蘇維埃主義成了國際主義的代名詞,而民族主義再度成為「民族機會主義」的同義語。【13】
蘇維埃十月革命的勝利,究竟是國際主義的勝利還是民族主義的勝利?其實這是國家主義的勝利!列寧和史達林所研究的「民族問題」從來都不是為了俄羅斯各民族的自決或獨立,而是為了布爾什維克黨如何利用民族主義浪潮來儘快奪取國家政權並壟斷一切權力。誠如霍布斯鮑姆所說,19世紀的「民族原則」大獲全勝,自中歐到東歐,多民族大帝國陸續崩潰倒台,「除了俄國之外,歐洲沒有任何國家是根據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問題』政策進行重建的。有史以來第一次,歐洲這塊拼圖幾乎全都是由民族國家拼湊而成,而且這些國家全都擁有某種資產階級式的國會民主。」【14】但是,惟獨由列寧和史達林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既不容許民族自決,也不容許民族自治,他們主張的國際主義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動員國際上的一切政治和經濟力量來為蘇維埃政權的長期存在服務。列寧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俄國工人階級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全部歷史,已經使它們具備了一切條件來採取『國際主義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徹底革命的策略。」【15】因此,斷言「民族主義的理論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歷史性的大失敗」,【16】是一個重大誤判。在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革命國家,民族主義的各種喧囂絕不會是民族自決或民族獨立的先聲,它們最後必定會被融入到國家主義主導的大合唱之中。
二、儒家視野中的「民族主義問題」
民族主義思潮及其運動是19世紀歐洲的歷史現象,它一方面因應於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另一方面又是因應於舊的王朝制度的覆滅。到了1922年,曾經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倫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奧斯曼王朝先後滅亡,取而代之的是中歐和東歐地區的以民族國家為模式的建國運動。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歐洲現代社會的起源,絕非是資本主義、理性主義和工業主義各自單獨作用的結果,而是一個「制度叢結」的過程,尤其是一個與「民族—國家」相伴隨的獨特社會整合的過程。【17】或者如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斯·托馬斯所理解得那樣,民族國家是16世紀以來歐洲歷史進化所達到的最高政治組織形式。【18】霍布斯鮑姆對19世紀以來歐洲風起雲湧的民族建國運動做了精闢的概括:
「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可說是19世紀歐洲歷史舞台上的主角,尤其是在『民族原則』以極戲劇化的方式重劃歐洲地圖的時期,亦即1830年到1880年,在這五十年間,就算他們百般不願,也不得不去面對由民族原則所引發的諸多問題:先是德意志和義大利的統一運動攪亂了歐洲列強苦心維繫的均勢局面;緊接著,奧匈帝國也基於民族原則宣告分裂(在簽定1867年的妥協方案之後);隨後是西歐的比利時與東南歐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日後分裂成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也紛紛要求基於民族原則建立主權國家;同時,波蘭境內也發生兩次暴動,要求依民族原則重新劃分領土,以便建立民族國家。這場波瀾壯闊的民族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