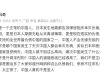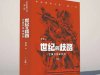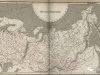國家命名,它本質上還是19世紀「前民族期」王朝國家的繼承人,這個基本判斷同樣可以用於說明中國在帝制崩潰之後的制度安排。中國與越南的戰爭,看上去像是一場民族主義戰爭,但實際上和以前中央王朝征服或懲戒其藩屬國的戰爭具有相似性:戰爭的目的既不是為了領土,也不是為了利益,而僅僅是為了維護中央王朝的禮儀秩序(面子)。中越的邊境戰爭從某種意義上看,可以視為一場「後帝國」的戰爭,它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徹底破產,同時又預示著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再度結合。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帝國式的中央集權國家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就成為迫切的理論需求。
中國改革開放是源於傳統的帝國式治理體系的失敗,改革初期,整個國家普遍進入到一種民族性反思狀態,不僅批判傳統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內在弊端,而且也深刻檢討傳統思想資源的問題所在,掀起了全面學習西方文明國家的先進位度、文化和價值觀的思潮,開啟了一個民族性自我否定和自我重建的進程。但是,隨著改革開放日趨顯示出巨大的經濟績效,國力日益增強,以及國際形勢和國際力量格局的重大變化,一種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在國人的精神層面成為主流,民族性自我否定和自我反思的進程被民族性的自我擴張和自我炫耀進程所取代。1981年,中國女排首獲世界冠軍,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這個口號代表著一種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懷,隨後迅速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1990年代中期之後,民族主義情緒在民間空前高漲,從「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到2000年之後發出了「中國即將統治世界」的聲音,民族主義成為了時代的主旋律,官方與民間之間的最大共識由此建立起來了。民族主義似乎重新塑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或一個「後帝國」的國家,按照安德森的「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的定義來問:民族主義的大肆泛濫是否可以想像為中國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了?
中國新左派的主要理論代表人物,如汪暉、趙汀陽、劉小楓等,之所以共同選擇以「民族國家」為主要批判對象,就在於他們比那些民間的民族主義者具有更深的理論直覺,他們意識到中國民族主義與歐洲民族主義的重大區別,是帝國與民族國家迥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以建立民族國家為目標,而毋寧是繼續保持一個強大的帝國式的中央集權體制。劉小楓在評述科耶夫的《法國國是綱要》一文中,把科耶夫重建法國「帝國」的政治抱負與「毛澤東的文明視野和政治行為」聯繫在一起,認為前者思考的並非是「現代性的既成形態——民族國家形態,而是新的『由加盟的民族國家』構成的『帝國性』聯盟。」這個「帝國性聯盟」表明:「民族性國家與『帝國性功業』之間存在著內在矛盾。換言之,『帝國性功業』具有文明性質,民族性國家則並非如此」。劉小楓對科耶夫重建法國「帝國性功業」的構想大加讚賞,主要是為了說明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構想」同樣具有「帝國性功業」的性質,他由此認為,完全可以把科耶夫《法國國是綱要》中的拉丁民族改成中華民族。【44】趙汀陽的「天下體系」理論,與劉小楓如出一轍,實質是企圖建立一種新的帝國敘事,如他自己所說,「天下/帝國」理論,表達的「正是關於帝國的一種理想或者說完美概念」,「天下/帝國」在正當性上遠遠超越了「民族/國家」框架,而中國的帝國歷史成了「天下/帝國」理論的藍本。【45】與劉小楓和趙汀陽相比,汪暉建構了一整套更系統和更全面的帝國敘事,他不僅試圖在滿清「帝國建設」和現代「國家建設」之間建立起一種歷史的延續性,而且也試圖證明兩者在制度建設上的統一性,即同時證明帝國的歷史和現實合法性。汪暉對「帝國—民族國家二元論」的批判,是認為民族國家敘事既不能充分揭示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帝國形態的性質及其運行,也不能將其視為帝國終極之後的現代國家模式。汪暉從奈格瑞和哈特的《帝國》一書和其他「帝國研究」中獲得的重大啟示是:「一個是對所謂『後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問題的思考」,「另一個則是從對民族—國家體制的不滿或反思出發而重新展開的『帝國研究』,它直接地表現在許多歷史學者對各大前現代帝國歷史的重新挖掘,以及對迄今為止仍然在歷史研究領域占據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國家及其歷史尺度為中心的敘述方式的超越。」【46】總之,用帝國敘事和「後民族—國家敘事」來反對或取代民族國家敘事,構成了汪暉的「現代中國研究」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正是從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汪暉並不認可以「天下」概念來取代「帝國」概念,儘管在他看來,「天下」概念同樣是為了回應對民族國家的質疑而提出來的,但「這一概念代表了中國的『獨特性』毋寧是從民族—國家的基本知識出發而展開的一種有關中國的特殊主義敘述,說不上是深思熟慮的結果。」【47】與此相比,「帝國」概念才是被汪暉認定為具有普遍主義性質,它不僅可以充分描述特定的王朝和政治實體以及中國政治文化的特徵,而且也可以作為現實的政治實體概念參與到世界歷史和世界體系的理論重構之中。從這個意義上看,汪暉是一個典型的「帝國主義」者。
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只有在帝國—民族國家的二元對立結構中才能看得清楚:究竟是帝國的民族主義還是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
四、從普世主義走向民族主義
中國新左派的同志們集體走向民族主義之前,幾乎都是一個「普世主義」者,或者信奉儒家普世主義,深信孔子的學說可以為人類萬世立法;或者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普世主義,深信共產主義理想一定能在全世界實現;或者信奉西方啟蒙主義開創的普世主義,深信自由、民主、憲政、人權是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應遵循的普世價值。因應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危機——它承諾的革命、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國際主義的諸項原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中瀕臨破產,從而導致它所提倡的普世主義失去了基本的理論信用。而儒家普世主義,在經歷了馬克思主義的長期沉重打擊之後,因應於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