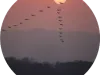鄭也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這十一個譯詞中,筆者看好"正份(或正分)"與"正權(或權正)"。比較二者,"正份"或許與right的詞義更貼合。而"正權"在被社會接受上,或許會沾到"權"字的便宜,畢竟"權利"一詞行使了160年。
辨析前賢的思考會增長我們的智慧。提出新的譯詞的衝動就是因為"權利"太糟糕了。能不能替代的第一條件是,有無好的候選。沒有則一切免談。而一個好的替代能否被社會接受,是超複雜的事情,我們大可只求耕耘不問收穫。
Right是法律領域中的核心詞彙。不幸的是近160年來,right的譯詞"權利",差強人意,卻一直當道。"權利"不具備right一詞中最重要的含義"正當"。而"利"的含義又是right所不具備。除了雙向的不匹配,"權利"的發音與"權力"完全相同,在口語表述中,為了不讓聽眾混淆,常常要特別說明此處是"立刀"還是"力量"的"li"。在書面語言中也有麻煩。縮寫是文字追求簡潔的慣常策略,但因兩"權"撞車,這裡行不通。如果寫到"我有權這麼做",讀者不知道你有"權利",還是"權力"。
其實從這個譯詞產生起就飽受批評,企圖取代者不絕如縷。本文意在點評right的諸多譯詞的得失,並提出筆者屬意的候選。
本,本分,理
1838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新加坡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收入《獨立宣言》,其中的right譯為"本,本分"。以後這本書修訂後於1861年在上海出版,其中的right改譯為"理"。"本分"和"理"的譯法都靠譜。
道理
1839年,查辦鴉片貿易的林則徐委託英國傳教士伯駕翻譯滑達爾所著《各國律例》。林則徐對其譯文不滿意,委託中國的譯員、馬來西亞歸國華僑袁德輝再譯。伯駕在翻譯《海國圖志》時,找不到與right對應的中文詞彙,以改寫方式行文,比如"維護自身的權利"被翻譯成"欲自保其身,自護其地"。袁德輝在翻譯right時大多使用"道理"一詞。
面對下面的英文:As then every nation has a right to chose she will or will not trade with another.伯駕的譯文是:"如外國帶鴉片往省,流毒射利,該本國不准他進口,亦不能告訴一說之事,此是理也"。袁德輝的譯文是:"各國有禁止外貨物,不准進口的道理。"
伯駕用了"理",袁德輝用了"道理",伯駕是改寫,而袁氏是以"道理"對應right。但袁德輝還抓不住這個關鍵詞的特徵,只好以泛概專。物理、數理、地理、病理、法理,其中皆有道理,right是哪一種道理?如此泛泛應對,自然不會被後來的翻譯家繼承。但他還是看到了right與power的相異,傳統的power常常不是因道理而上位,且在位時也常常不講道理,故以"道理"對應"權力",也算勉為其難。
權與權利
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領銜翻譯的《萬國公法》出版。後世公認在這部譯作中,第一次出現right的譯詞"權利"。這麼說沒錯,但是今人茫然無知的是,"權利"遠不是丁韙良的首選譯詞。
楊焯女士的《丁譯<萬國公法>研究》紮實地比照了原作和譯作,在《清末西方法學概念的傳播與衍指概念的形成》一文中指出:原作中的right,譯作"權"多達70次,譯作"權利"才區區4次。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埋沒在譯作十萬言中的如此稀少的"權利",何以讓後人將丁韙良的名字與"right—權利",而非"right—權"聯繫在一起。這或許是因為丁韙良翻譯《公法便覽》(1877年出版)時譯詞的重大改變。
楊焯女士正在著手這個譯本的研究。她說,《公法便覽》中丁氏基本上將right譯為"權利",譯本中"權利"出現174次;priviledge大多改譯為"權"或"威",只有6處譯為"權利",如"公使、商船、土著"之"權利"。費解的是,丁氏在《公法便覽》的凡例中說:"原文內偶有漢文所難達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覺勉強。即如一'權'字,書內不獨指有司所操之權,亦指凡人理所應得之分,有時增一'利'字,如謂庶人本有之權利。"他不提本書中譯詞的改變,卻似乎在為當初《萬國公法》的翻譯辯護。而他為譯詞"權"的辯解是無力的。"權"的詞源是"秤砣,權衡",這或許是丁韙良團隊選擇它的原因。但當"權"很早就衍化成社會博弈中的詞彙後,指的是統治者的"權力"。
丁氏強調他的"權"覆蓋"有司與凡人"是一廂情願,中國讀者當然按照"權"在中國的含義去理解。中國助手們或許茫然西方的概念,丁氏絕對明白power與right的分野,二者是絕不可以翻譯成同一字眼的,可是偏偏發生了。即使看到power與right在法理中的姊妹關係,願意在right的譯詞中連帶"權"字,也一定要綴上一個字,以區別"權力"。選擇很多,比如"理""民""正"。
丁韙良翻譯《萬國公法》時有何孟師等四位同文館的學生作助手。沒有他們,丁韙良不知道在晚清幾近絕跡的"權利"一詞是大概率的事情,他們偏偏為"權"後綴了與right沒有一絲關係的"利"。在《萬國公法》中頻次不高的"權利"還同時成為priviledge的譯詞。十餘年後,丁韙良擺脫了此前翻譯中的雙重混淆,"權利"成為right的專一譯詞。
權理
1865年丁譯《萬國公法》在日本印製,成為日人研討法律的最初資源。很可能是這部書在日本開啟了right的討論及其譯詞的選擇。日本平凡社1988年版《世界大百科事典》"權利"詞條說:right初時譯為"權理",並說該譯法較"權利"為優。津田真道在1866年把right譯為權利。福澤諭吉反對這種譯法。加藤弘之1870年出版的《真政大意》將right譯作"權理",得到好評。明治6年(1873)5月15日太政官布告第162號使用"權理"作為官方表達。1868年西周翻譯的《萬國公法》出版,其中的right譯作"權",這是因襲丁氏的翻譯。後發覺譯詞"權"混淆了power和right,在《生性發蘊》(1873)和《致知啟蒙》(1874)兩部譯作中,徹底改用"權利"翻譯right。其轉變的時間居然早於丁韙良翻譯《公法便覽》。1894年德國人耶林的影響巨大的《權利競爭論》(1872)經宇都宮五郎翻譯在日本出版。
自此"權利"一詞風靡日本。就是說,日本人曾經在right譯詞上面臨著三種選擇:權,權利,權理。"權理"最好,因為"理"中包含right中"正當"的意思。並且"權理"也好過"道理",因為它將寬泛的"道理"限定在"法理"的範疇中。"權"最壞,因為它混淆了right與power。最終日本人選擇了"權利"。當然,日語中"權利"與"權力"不同音,這導致"權利"在日本的使用沒有在中國語境下這麼糟糕。傳教士的譯作是東亞引入西學的第一波。更好的翻譯必由本土譯者完成,因為譯文定格在母語。
而在第二波中,中日差距巨大。中國這邊只有嚴復等幾個人,日本那邊是一個龐大的翻譯群體完成了驚世的浩大工作,他們常常就一個譯名研討很久。筆者相信,日本學術界日後對當時的抉擇一定有過深入的研討。這也是今天中國人反省right的譯法時應該了解的。如果當時日本選擇了"權理",並影響到中國,應該是我們的福音。
right概念最初引進時期,在中國沒有,在日本卻引發了社會運動。1875年小室信夫等人請願要求成立國會,他們主張普通百姓也有"權利"。這些社會運動給留日中國學生深刻印象。20世紀初葉大批西學概念經過日本進入中國。"權利"亦在其中。日本留學生的《譯書彙編》第一期(1900年12月)上刊登了《權利競爭論》,應該是從日譯本轉譯。梁啓超的文章以《權利的思想》(1902)命名,文中大段引用耶林。
如果沒有"權利"從日本強勢返銷,中國人面臨著丁韙良先後使用的兩個譯詞:權與權利。"權"一定會被淘汰。而丁韙良後來確定的"權利",也未必會被後來的中國人繼承。本土學者有可能找到更好的譯詞,從嚴復的批評就可以看出。
可惜,從日本返銷的"權利"比本土學者的努力早了一步。
直
1902年嚴復在給梁啓超的信中批評"權利"譯詞。如果我們搞明白嚴復對這個譯詞的批評是針對誰,亦可幫助解答一個爭論:丁韙良和日本人哪方面在這個譯詞上對嚴復時代的中國影響更大。
嚴復在信中說:right的譯詞"權利"是"以霸譯王",他幾年來在苦思譯詞。先考慮"職",後擔心與duty混淆。以後看到了高郵對《詩經》"爰得我所,爰得我直"的解釋:直與職通,直可解釋為所(兩句譯作白話文均為:才得到我的所在)。他驚喜"直"與right三處相通:一物象之正,二道理上的正當,三"職、所"與"應享之處"的對應。故云:"以直字翻right尤為鐵案,不可動也"。
以上論證極其雄辯,說明本土最優秀的譯者已經高於傳教士和日本人。
但是動搖的恰恰是他自己。在他翻譯《天演論》(1895年動筆)時,對應right處,有時譯"直",有時譯"權利"。以後的幾部譯作統統如此。雖然他還造了兩個新詞:"天直"和"民直",以避免"直"字的費解,卻沒有改變有時也使用"權利"。
筆者的分析是,當嚴復陷入考據時,他看到了與right貼合的漢字非"直"莫屬。而當他回到現實生活,他明白詩經的時代太遙遠了,其語言已經不是晚清人所易理解,他只好順應世風。因《天演論》而更改姓名的胡適評價其人:嚴復的英文和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嚴復敗在了中土白話文大潮將起之時代,敗在了早他一步的日本譯詞與白話文順利接軌。
義權
1933年胡適撰文《民權的保障》,文中說:
其實,權利的本意只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後來才變成法律給予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中國古代思想也未嘗沒有這種"義權"的觀念。孟子說的最明白: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正是權利的意義。"一介不以與人"是尊重自己所應有;"一介不以取諸人"是尊重他人所應有。
筆者以為,"義權"好過"權利",但依然不妥當。主要問題是"義"的道德色彩過重,儘管它也包含道理的意思。孟子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兩處的"義"都顯然是道德,而不是right。right不是道德。如果占有這筆財產是你的right,那麼你用之做高尚還是低下的事情都不影響你的right。"義權"會讓人聯想到高尚的追求,而不是底線的保障。
胡適大概是意識到"權利"的譯法已經無法扭轉。他只是說了上面那番話,文章中無數次使用"權利"一詞。
利權
1992年,夏勇在其《人權概念起源》一書中說:
現代漢語中的"權利"一詞,準確地講,應該改寫成"利權",即"利之權"。"權"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裡,都含有"正義"和"權威"的意思。倘若個人利益喪失了在道德上的正當性和權威性,便不可能生發出現代意義的權利概念。
筆者以為,"利權"只在一點上好過"權利",就是避免了二者發音上的混淆。在意思上二者極為相近,在字典中筆者未見"權"有"正義"的意思。"利權"一詞在19世紀末葉清朝皇帝的上諭和大臣的奏摺都多次出現。金觀濤、劉青峰討論權利的文章中引用朝廷中"利權"的使用12次之多,意思均為"經濟利益和財政大權"。right的覆蓋遠比"經濟財政"寬闊。信仰和言論的right,殊難歸到"利權"的含義中。
權分(份)
2006年吳思在《洋人的"權利"我們的"分"——譯名選擇與傳統斷續》中提出"權分"或"權份"的譯法。吳思在文章中說:
1877年譯完《公法便覽》,丁韙良在凡例中寫道:"'權'字……亦指凡人理所應得之分"。他既然想到了"分"字,又給出了如此精當的解釋,為何不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
閱讀right漢譯歷史中筆者發現與"分"擦肩而過的不只丁韙良。吳思深入細緻地分析了古今漢語中"分"字與right的吻合,以及"分"比"權"的優勢——接歷史,接地氣,且給出了right之下的自主空間的感覺。吳文在這些方面極其雄辯。
但筆者以為,在尋找漢譯字眼時,"分"可以替代"權",也只是替代了"權",二者放到一起也無補一個缺憾,即彼此都不具備right中的"正當"的含義。而"分"這個古老詞彙有其沉重的歷史負擔。"君臣之分"融入中國人的血液,乃至中藥中不同成分的主次關係都要借用"君臣之分"。而"君臣之分"中只有界限,沒有人的基本right。"分"字無法擺脫這種認命的、放棄平權追求的意識。吳文清醒地意識到"權分"的局限。他說:"權分在國人心中喚起的感覺,與right在歐美人心中喚起的感覺一樣嗎?'權分'真和right全等嗎?恐怕仍不相等。……不解決有名無實的問題,僅靠語言技巧肯定是不夠的。"
天權
這個譯名是我在2021年6月10日發表的一篇小文《挑戰"權利"的譯法》(載於《南方周末》)中提出的。文中說:
6月3日,我與單純先生、張大中先生見面。聊天時我提出了"權利"譯名的荒謬。單純當即搭腔:"權利"是丁韙良1864年主持翻譯《萬國公法》時確定的。他漢語水平提高後就後悔了。單純接著說:right應該譯為"天良"。我並不同意。但"天"字打動了我。我思考"權利"有日,且曾鍾情"正權",故單純先生"天良"一語落下未幾,我就高聲回應:"天權"。他那廂幾乎是立即作答:"天權好"。兩雙手立即握在一起,共祝我倆合成的新譯名。
文章發表後很快收到吳思的來信,發來了本文剛剛討論過的《洋人的"權利"我們的"分"》。讀後我知道了自己的草率,他的文章要厚重得多。長考後我放棄了"天權"的譯法。因為意識到right中沒有"天"的意思。"正當"要比"天"寬闊。"天賦"只是"正當性"來源之一。
正分
讀過吳思的文章,否定了"天權"後,我和吳思辨析他的"權分"。我說:叫"正份"好;這是個新詞,但它的反義詞"非分"無人不知,"非分"可以幫助人們聯想、熟悉和接受"正份"。
吳思通話中接受我的主張,並希望我把這些寫下來。這迫使我進一步閱讀和思考,遂有本文。
正權與權正
我在《挑戰"權利"的譯法》中說:
我曾經想到的譯名是"正權"。它匡正了"正當"之義在"權利"中的缺席。後來才知道嚴復1903年翻譯密爾的《自由論》(嚴復譯為《群己權界論》)時說:將right譯為"直"最好。很高興我與前賢所見略同。但不幸"正權"與"政權"同音。而"政權"是流行且強勢的詞彙。"正權"若問世,必定在聽眾那裡產生更大的混淆。故敝人向朋友提出這個譯名後,不待他人反駁,自己就打了退堂鼓。
這番長考後我改變了認識。我認為"正權"是很好的選項。與"政權"同音的問題,遠沒有"權利"與"權力"同音的後果那樣嚴重。因為後者在大多數的口語場合真的無法區分。而前者不同。前者在多數語境中是可以區分的。比如"這是你的zheng權""槍桿子裡面出zheng權"。人們聽得懂前者指"正權",後者指"政權"。再者,"權利"與"權力"在出現頻次上都很高,而"政權"出現的頻次低得多。故幾乎不會有麻煩,至少要比"權利與權力"好得多。
在意思上,這個詞彙的搭配極好:"正"意指正當,"權"意指在正當範圍中的自主性。如果不滿與"政權"同音,這裡還有一個"正權"的變種,就是"權正"。它也是漢語中的一個詞彙,只是少見。其意思是:權變與常道。《北史·魏紀一論》:"帝孝心叡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歷史文獻中筆者只搜尋到這一次使用。很可能其詞義的解釋就是根據《北史》中的這句話。而"權變與正道"相似於"正當性與自主性",這正是right在法理上的核心含義。"權正"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在語詞上與"權力"構成鮮明的"正與力"的對位。
在以上十一個譯詞中,筆者看好"正份(或正分)"與"正權(或權正)"。比較二者,"正份"或許與right的詞義更貼合。而"正權"在被社會接受上,或許會沾到"權"字的便宜,畢竟"權利"一詞行使了160年。
辨析前賢的思考會增長我們的智慧。提出新的譯詞的衝動就是因為"權利"太糟糕了。能不能替代的第一條件是,有無好的候選。沒有則一切免談。而一個好的替代能否被社會接受,是超複雜的事情,我們大可只求耕耘不問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