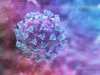第八個問題,能不能說「沒有十年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得益於比較社會主義體制的觀察研究。早在1980年代中後期,有些外國學者就論說:鄧小平那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大徹大悟(今天看起來更顯得是如此),決定性的來自於他們本人及家屬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若無文革把中共1949年以後建立起來的那些體制和政策折騰得亂七八糟,也許中國就和蘇聯一樣,在傳統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一步步延續下來。可是十年文革這種翻天覆地的衝擊,令那套傳統體制沒辦法照常規支撐下去,改革開放於是就成為高層的明智選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全世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率先走出一條不同於它的姊妹國家的半資本主義道路、主動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功不可沒——物極必反。
第九個問題,缺乏強韌法治體系的政黨或政權內部進行嚴酷的清洗——不論用什麼術語去稱謂,比如說「吐故納新」、「黨內鬥爭」、「爭權奪利」、「窩裡鬥」等等,並不是中國的獨家傳統。僅僅就執政的共產黨體制的範圍里看,蘇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紅色高棉短短的幾年在台上、朝鮮自從1940年代後期至今,皆有類似現象。但是,用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來進行這樣的清洗,至今唯有在毛澤東統治的最後期。那麼,這些中外黨政軍體系內部的「吐故納新」的相同和相異是在哪些方面?為什麼?這個問題是所有以上諸問題的精髓。
以上的九個大問題都是濃縮過的,每一個都包括了兩個或更多的子問題,而且大多數都沒有確定無疑的答案,包括筆者本人也無法解答很多讀者和文革課堂里學生們提出的相關探問。香港的大學生們十幾年來,每年都抱怨上筆者的文革課程要讀那麼多的中外文書籍和數碼資料庫文件(即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發行的全套資料庫),還有好多具體問題解答不了。首要的原因是至今有關中國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資料,一直沒有對外開放。海內外眾多中文報刊雜誌在2008年11月底,興奮地報導了「北京的文革檔案將於今年底向公眾開放」。大約一個月以後,在香港註冊但可以在中國內地發行的《鳳凰周刊》,宣告「中國大陸文革檔案暫緩開放」。當時筆者在北京,研討會上學者們感嘆,「暫緩」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到了如今,更沒有絲毫跡象會發生這樣的公開檔案的大好事。
香港雖然幾十年裡一直是全球有關文革的中文資料的出版發行重鎮,然而至今我們也沒有見到,文革最重要的領導者、犧牲者和倖存者——毛澤東、劉少奇、彭真、周恩來、林彪、鄧小平、江青、康生、張春橋——曾經發表過文革的回憶錄。但所有這些不足之處,並不影響我們把以上整理的毛澤東之「夢」的大致內容,作為對照的一面鏡子,再把當今的「中國夢」之官方版呈現的內容,作為另一面鏡子,仔細看看這兩面鏡子之間,互相反光折射到了何種細微的程度。正如在本專欄上一篇評論里所說的,經過這樣的對照,從兩組要素(兩面鏡子)及其延續和演變,我們才可能理性地回應那個「文革是否再來一次?」的沉重提問。
(三)
現在筆者把前兩篇討論的毛澤東之夢作一總結,可以把其中的諸多要素歸納成三大單元。第一個大單元是關於「中國社會」,第二個大單元是關於「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第三個大單元是關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三大單元的構成要素是我們展望未來的出發地。
非同尋常的中國社會
先看第一大單元:此處的「中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經濟和文化教育領域。在毛的設計圖裡,理想的中國社會是全民皆兵、全國變成一個超級軍營。對毛澤東之夢的這個部分,林彪把握得最貼切,所以從1960年代初開始,林就反覆宣揚,全國各行各業都要學習解放軍,人人都要像士兵一樣「一切行動聽指揮」(《中共中央批示,1960年12月21日》。丁按:這是毛對該年10月20日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的高度贊成和全面推廣)。全國變成一個超級軍營的試驗,早在1958年大躍進初期已經著手,經濟的崩潰使之半途而廢。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該試驗又被提上桌面,「五七幹校」、「大寨樣板」、「大慶樣板」等都與之相關。全國變成一個超級軍營,其物質基礎當然是指令經濟,所以它應該被視作「軍事共產主義」體系的落實。中共執政後毛一直試圖把國民經濟推向這個軌道,考慮以配給製取代工資制,卻因預算太高未能付諸實踐(參閱毛親筆點評和推薦的張春橋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文革中毛多次告誡:工資制是資產階級法權,不能讓它無限期實施;商品經濟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必須予以限制。指令經濟下的中國當然無法和世界貿易體系連通,所以毛督促全國「自力更生」。至於文化教育領域,毛更不想中國交流外國,無論是資本主義的(西方),還是修正主義的(蘇聯東歐),都必須徹底掃除其影響。
當今官方版的中國夢裡,有多少上述「毛夢」的要素呢?讓全國人民服從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這顯然是歷屆政府都願意做到的。不論是以「維穩」的名義,還是以「平安中國」的名義,更遑論眼下國際上議論紛紛的「數碼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的管控模式,都旨在把民眾的言行約束到整齊劃一的程度,雖然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靈活性有些差別(Samantha Hoffman,「Managing the State:Social Credit,Surveillance,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JamesTown.org,17 August2017)。在文化教育領域裡阻隔外國的影響,當今的中國夢裡只有一半的「毛夢」,即反對「普世價值」。教育上中國關不住大門,作為全球外派留學生總量第一大國的地位,延續已久,還會保持多年。實施軍事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制,當今延伸下來的只有其中一塊,即關係到強軍的戰略資源和保證政權永固的支柱產業。換言之,「國計」的一塊是軍事共產主義的延伸,「民生」的不再是。
小結:「毛夢」里的中國社會設計,連接到當今中國夢裡的要素,尚不及一半。即便未來十年形勢更為嚴峻,也不會超過一半。我們只要把毛的「五七指示」等文本和毛的幾次試驗與當今中國社會兩相對照,以上判斷就能站得住腳。
中國全面對抗世界
再看第二大單元: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自從史達林去世後,毛澤東日益強化的一個信念,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避免地從莫斯科轉向北京,毛是共產主義譜系的第三座里程碑(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座,列寧史達林是第二座)。1960-1970年代毛力主輸出暴力革命,號召美國黑人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大本營,林彪把毛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上升為全球革命道路、即第三世界包圍第一世界實現世界一片紅(「在首都人民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會上林彪同志的講話」,人民日報1967年11月7日),都是毛努力實現其顛覆世界夢的亮點。
儘管當今「中國威脅論」四處冒煙,但幾乎沒有嚴肅的觀察家評論家認為北京正在輸出暴力革命。中國目前和外部世界發生糾紛的,主要是源於這些:輸出產品或產能、輸出發展模式包括環境污染、輸出資本、輸出大外宣、輸出治理模式。這幾種輸出也令很多老外擔憂,但它們不同於暴力革命的輸出,後者是要推翻「帝修反政權」,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要掀起多年的戰火和流血;前者則主要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是你輸我贏的競爭(「我們為何不應學習中國模式」,《新蘇黎世報》2018年2月5日評論,DW中文網同日翻譯轉載)。未來十年或更長時段里,看不出中國會朝世界革命的道路邁進。中國當今的這些做法,一大半是從西方學來的,是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許多已開發國家都做過,如德國和日本(Joshua Aizenman and Rajeswari Sengupta,「Global imbalances:Is Germany the new China?A sceptical view」,VoxEU.org,5 October2010)。最關鍵的是:當今中國的這些做法,是盡力在國際市場體系里多占好處,而不是摧毀它,像蘇聯陣營那樣以社會主義貿易體系取而代之。目前中國最高層每天向世界大聲呼喊的,是要推進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度集權之後
最後看第三大單元:中國的政治體制。「毛夢」裡面的幾大單元,在毛生前就數這個單元落實得最給力,用林彪的話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批示》,1966年9月22日,發至縣、團級學習文件,筆者學習後收藏)。毛畢生造就的這種政治體制,對後人影響巨深。哈佛大學商學院1990年代後期曾經在中國大陸對工商界中上層做過一個實證研究,發現他們最嚮往的領導體制即最想仿照的,就是毛模式,不論他們是否在毛時代挨過整受過苦,也不論他們是國企主管還是民營老闆。有了這個普遍性的背景,我們對內地這幾年日益強調權力集中再集中的趨勢,就不該驚訝了。
綜合來看,毛澤東之夢和當今中國夢的關聯程度,以第二大單元最弱,第三大單元最強,第一大單元居中,這種整體格局對我們的未來意味深長。公眾注意力顯然一直是聚焦於第三大單元,恰如今年3月初北京「兩會」前後的萬千報導和評論所示。由於關注點一直偏重於此,無數人就擔心中國不久「文革會再來一次!」筆者卻不作這樣的判斷,理由簡述如下:當今中國夢的核心內容無法藉助「全民皆兵、全國成為一個大兵營」的毛式中國社會結構來實現,更不可能藉助於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兩個陣營、你死我活鬥爭」的毛式全面對抗來完成。以「兩個一百年」為時間框架的中國夢若非全盤落空,至少三種運行機制是必不可少的——持續造富的國民經濟,哪怕這個經濟體裡面充斥不公正和不平等,哪怕多位企業家個人的下場是個悲劇;持續注入中國經濟的創新元素,不論是經由留學渠道或人才引進或專利購買或技術竊取;持續提供給中國巨量產能及產品對外輸出的渠道,不論是通過國際市場的公平競爭或是通過一帶一路之類的國家資本主義大手筆操作。這三種運行機制可以在一個更自由的政治體系里更有效地起作用,也可以在一個更強制專權(Hard-authoritarian)的統治體系里以更高的成本起作用,但它們絕對不可以在一個原教旨主義環境和極端主義體制(文革期間便是這種綜合狀態)里掙扎生存。
有理由保持艱難和頑強的樂觀主義
筆者堅信,當今的中國夢之落實,必須依賴企業家階層、國際貿易商階層和專業技術階層,儘管北京頂層不會讓他們把自己的行業資源和專業能力轉換成對黨國權力體制發出挑戰的手段。香港未來之生存發展的空間與局限也與此一脈相承——這三個階層是香港社會的支柱群體,他們的相對優勢是世代競爭形成的,難以被替代取消。他們活動的「天花板」早先(1997年之後的十多年)是玻璃做成的,而現在越來越換成是鋼板材料的了,明擺在那兒,不許去碰撞。只要不去正面碰撞,就不至於摧毀你。
有些讀者或許要問:為什麼當今的中國夢不至於全方位對接毛澤東之夢?為什麼第三大單元再趨強化,也不會演變成文革全盤迴潮,決不會主動毀掉上述的三種運行機制及它們的三個操作階層?這組問題已經超出了政治社會學的經驗討論範疇,進入到宗教學層面,比政治哲學更加形而上,只能留待以後再作詮釋。
(有刪節)
(香港《信報月刊》,2018年1、2、3月號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