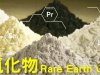伍子胥獻「三分疲楚」策略,吳國以小搏大
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親自率領3萬精銳部隊伐楚,五戰五捷,長驅直入,一度占領楚國郢都。楚國上下在滅頂之災中團結起來,反抗吳軍暴行,秦哀公發兵援楚抗吳,吳國內部發生了夫概叛亂,還受到越國重兵襲擊,結果吳軍大敗而歸。
關於伍子胥向吳王闔閭奉獻的攻楚之策,《左傳·昭公三十年》記載,吳王闔閭問伍員:「『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蔽。亟肆以罷(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這就是伍子胥提出的「三分疲楚」策略,事在公元前512年。
在這裡,「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是伍子胥對楚國政情的判斷,意思是說,楚國執政的官員多,他們互相不和,沒有一個敢於承擔主要責任。伍子胥認為,針對楚國政情,如果把吳軍分為三部分,輪流騷擾楚軍,吳軍一部分出擊,楚國必定調動全部兵力應戰;等到楚國軍隊開過來,吳國軍隊主動避讓,讓楚軍撲空。然後組織第二輪進攻,迫使楚軍處於持續緊張狀態之中,陷入疲於奔命、勞累不堪,將士將普遍厭戰,戰鬥力受到極大削弱。「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使楚國及其軍隊極度疲乏,無法弄清我方意圖,然後集中兵力,發動總攻,必定大獲全勝。
荀罃首倡「三分四軍」,加強晉國防禦
伍子胥的「三分疲楚」策略,受到晉國方面軍統帥荀罃「三分四軍」戰術的啟示。
晉楚兩大諸侯國戰爭不斷,鄭國夾在中間,成為雙方爭奪的目標。在爭奪鄭國的戰爭中,楚國運輸線很長,晉國後勤供給線較短。公元前564年,晉國中軍帥荀罃提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大意是說,把晉國的四軍分為三部分,聯合諸侯的精銳部隊,用以迎擊楚軍;我軍以逸待勞,將士精力充沛,而楚軍遠道而來,體力和給養不能與我軍相比,因而不能投入戰鬥,這樣,(戰爭減少)比兩軍不斷地交鋒好得多。長期用大量人命來拼,不可以作為爭奪勝利的策略,那樣做的話,後面更大的勞苦和傷亡,永遠沒完沒了。(減少戰爭和傷亡)自古以來的法則,要依靠君子的智謀。按照荀罃「三分四軍」的主張,晉國把上軍、中軍、下軍、新軍分為三部分,並設立總預備隊,總預備隊用以應對前線不時之需,為前線補充兵員,所以稱為「三分」而不稱為「四分」。「四軍」是指當時晉國的四個方面軍,即上軍、中軍、下軍、新軍。「三分四軍」策略重點在於輪流出動三分之一的兵力騷擾楚軍,誘使楚軍不得不常年處於被動應戰狀態,加劇楚軍所處劣勢地位,使其將士疲倦厭戰,消耗其主動進攻能力。而晉國軍隊積極主動、堅持不懈地騷擾、挑戰,但不與楚軍決戰。同時,軍隊的三分之二正常訓練,養精蓄銳。貫徹這個策略,晉國加強了對楚國的防禦。鄭國雖然仍然在晉楚間搖擺,但明顯偏向晉國。
晉悼公採納「三分四軍」之後不久,提出予民休養生息政策,兩者結合施行,收到積極效果,晉國一度恢復霸主地位。「三分四軍」是春秋晉國歷史一個亮點。
吳國的戰略戰術
伍子胥的「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頗有運動戰戰略戰術思想,在冷兵器時代,可以算得上一個戰略戰術構想了。其一,「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表達的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積極尋求戰機,騷擾敵人,打擊敵人,迷惑敵人,削弱敵軍的戰鬥力,具有戰術性質;其二,「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主要是表達想要達到的目標,具有戰略性質。伍子胥的設想,在反覆、接連、持久地進行攻擊、騷擾之下,使楚國及其軍隊極度地疲乏厭戰,緊接著集中兵力,組織大規模進攻,必定能夠大獲全勝。這當然只是伍子胥的戰略期待。
從實戰來看,公元前584年到公元前504年,80年間,吳楚爭戰25場,吳勝17場,楚勝5場,兵鋒未交3場(均因楚國內部原因,或發覺吳軍戒備嚴整而退兵)。吳楚之間的二十多場戰爭,吳國失利次數較少,證明伍子胥概括的戰術正確反映了吳楚數十年交戰的經驗,是成功的。
但是,作為戰略,吳王闔閭和伍子胥、孫武子,沒有能夠創造實戰支持。公元前506年吳國軍隊破楚入郢,燒毀庫存的糧食,砸碎象徵楚國王權的九龍之鐘,首領們「以班處宮」,霸占楚王宮室和大臣妻妾,總之,吳軍一夜之間變成了凶神惡煞,戰爭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各諸侯國對於吳國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破楚入郢作為一個成功戰例,存在時間很短。
而公元前505年秦楚聯軍打敗吳軍卻具有戰略意義。
吳軍暴行激發了楚國軍民的反抗,君臣團結起來,普通百姓人自為戰。吳軍處處受到襲擊,3萬人無法有效占領郢都。秦哀公應楚國使臣申包胥之請,決定派五百乘兵力援楚抗吳。秦楚聯軍夾擊吳軍。吳國內部又發生了夫概叛亂,再加上越國重兵襲擊,闔閭不得不退兵回吳,以徹底失敗結束這場戰爭。伍子胥「三分疲楚」策略的戰略目標「必大克之」最終落空,一敗塗地。
范仲淹抗遼「十六字訣」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乞修京城札子》(一、二),是范仲淹分別於慶曆二年、四年(公元1042、1044年)向宋仁宗的兩次建言,主要論述修建汴京(開封)城防工事的重要性、必要性。當時北宋面對兩股強敵,一股是西夏,一股是東北契丹人的遼國。汴京遠離西夏,但與遼國距離比較近。范仲淹非常擔心契丹對汴京安全的威脅。契丹是一個強悍的民族,在俄羅斯民族看來,契丹就是中國,俄語直到現在仍然用「契丹」兩個字的諧音稱呼中國。
北宋經常辯論首都選址問題,有多個備都,汴京也稱東京,還有南都(現在的商丘),河北大名為北京,洛陽是理想中的都城。范仲淹《乞修京城札子》(二)認為,洛陽的地望適合作為都城,應該從長計議,把洛陽城防建設好,並在洛陽建設國家府庫,儲備糧食,等待適當時候定都洛陽。但是,遷都茲事體大,未可輕舉,當時最現實、最緊迫的問題是要加強汴京城防,確保朝廷安全。把汴京城防修好,高城深池,朝廷安全才有保障;即使兵臨城下,也有時間調兵遣將,可以拒絕遼方歲幣、割地等無理要求;然後對入侵遼軍實施「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追蹤)之」的「十六字訣」,即對入侵遼軍進行騷擾,使之不得安寧,難以立足,疲憊不堪,戰鬥力日漸消耗,無法縱深侵犯。如此,契丹將不敢覬覦汴京。范仲淹認為,這是「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范仲淹《乞修京城札子》(二)結尾特別強調,這是「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修好東京城防,實施抗遼「十六字訣」的機會也創造出來了。
范仲淹抗遼「十六字訣」是對付契丹的輔助策略。范仲淹抗遼「十六字訣」繼承了伍子胥以弱勝強,騷擾敵人,使敵人疲憊不堪的思想,也包含持久戰思想,不求速勝,貴在堅持,拖垮敵人,等待時機,戰而勝之。在文字表達上,把「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加工潤色為「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句子工整、排比、上口,便於言說,便於記憶,便於傳授,便於將士掌握運用。到此,「十六字訣」已經成型。
朱德毛澤東遊擊戰爭「十六字訣」
朱德、毛澤東著名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是中國共產黨軍事理論建設第一塊基石,是靈活機動戰略戰術的最初建樹。
古今兩「十六字訣」源於「三分疲楚」
中國幾千年經歷了無數戰爭,也積累了豐富的戰爭經驗,「十六字訣」源遠流長,是中國數千年戰爭經驗的繼承和發展。貴刊曾發表文章爭論「十六字訣」的發明人是朱還是毛,我覺得沒有意義,在雲南講武學堂受過正規軍事教育的朱德和飽讀中國古籍的毛澤東應當知道我這裡說的情況。筆者認為,朱德、毛澤東遊擊戰爭「十六字訣」的源頭,是伍子胥的「三分疲楚」策略。
首先,伍子胥的「三分疲楚」取攻勢,積極尋求戰機,削弱敵人,壯大自己。范仲淹抗遼「十六字訣」對入侵遼軍也是取攻勢,取驅除韃虜態勢。朱德、毛澤東遊擊戰爭「十六字訣」同樣取攻勢。三者有共同的靈魂。而荀罃的「三分四軍」取守勢,是防禦性策略;因此,朱毛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的源頭是伍子胥的「三分疲楚」,而不是荀罃的「三分四軍」。
第二,當時吳楚相比,無論國力、兵力,不僅吳小楚大、吳弱楚強,而且相差相當懸殊。而晉楚兩大國長期勢均力敵,無論經濟、政治、軍事還是文化,都是春秋時期南北爭霸的主角,「三分四軍」使晉國在與楚國的強強對抗態勢中稍勝一籌。而吳國實施「三分疲楚」,靠靈活機動的戰術以小搏大、以弱勝強,用智慧和創造精神戰勝敵人。范仲淹抗遼「十六字訣」、朱德、毛澤東遊擊戰爭「十六字訣」都含有以弱勝強的意義。
第三,在文字表達上,荀罃的「三分四軍」沒有名言警句的光彩,而伍子胥的「三分疲楚」初步具備了名言警句必備的思想之光、語言之玉、文字之珠的品格,含義豐富,讀來上口,易於傳播。古今兩個「十六字訣」具備了名言警句的特徵,透露出對於「三分疲楚」思想和表達形式的繼承發揚。
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伍子胥提出「三分疲楚」戰略戰術之後,公元前511年、公元前508年對楚國打了兩場勝仗,緊接著公元前506年的破楚入郢之仗幾乎使楚國滅亡。破楚入郢,雖然曇花一現,畢竟短暫閃現了「必大克之」的期待,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戰例,強化了「三分疲楚」的內涵和影響力,所以認定「三分疲楚」為源頭理由更加充分。
透過范仲淹抗遼「十六字訣」,可以看到伍子胥「三分疲楚」的影子,而朱德、毛澤東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則與范仲淹抗遼「十六字訣」非常接近了。把三者放在一起,它們的源流關係就顯而易見了。
《炎黃春秋》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