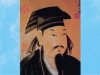紹興人在北京托人走後門花的錢,只是推動請託方式運行的一小部分費用,因為它只涉及到吏員「工轉干」這一條途徑,不過是明朝選官的數條途徑之一,並且還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徑。至於推動整個「請託制」運行的費用總額有多大,當時沒有正式統計,我現在也很難估計。但我們知道,在孫丕揚上任前的嘉靖年間,也就是《醒世恆言》中寫到的「飛過海」流行年代,吏部的一個吏員的肥缺就價值上千兩銀子,相當於當時一個縣太爺二十年的名義工資。權貴們收了人家的厚禮,經常點著名安排某個人到某個位置。另外,在孫丕揚生活的萬曆年間,如果某人從官員的位置上退下來,你想讓他推薦你接任,即使你的學歷資格年頭全夠,這筆推薦費也要五六百兩銀子,大概相當於一戶自耕農二十年的收入。上邊這兩個例子不過是群豹身上的兩塊班點,明朝文職官員的「崗」在兩萬個以上,吏員超過五萬五,武職更超過十萬,這兩塊斑點的大小,可以幫助我們管窺和推測請託費用的整體規模。
這筆官場上的巨額投資,最終自然要從老百姓身上一錢一兩地撈本取利,《醒世恆言》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
請託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的道理還可以再推進一步,因為明朝的官員工資甚低,不應該有很多銀子,銀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須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當然也可以像《醒世恆言》中說的那樣,大家先湊錢買個官當,按入股的比例分贓——這就意味著貪污準備最充分、貪污壓力最大的人最可能當官。這顯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門裡充滿了貪官污吏和結夥打劫強盜,動輒敲詐一二兩銀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見窮山惡水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孫丕揚想一想,就會發現他膽識過人。
掣籤法一出,請託無處容身了,那些權貴,包括孫丕揚的那些花大錢鑽營進來的部下,都斷了一條財路。沒有過人的膽量,或者頭上有許多小辮子被人家攥在手裡,誰還敢做這種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斷了自己的財路,誰又肯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此外,論資排輩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的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論資排輩加抽籤。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至於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抓鬮,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最後還有一條好處,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圍攻,說他的壞話,造他的謠言,保護自己即將到手的利益。
事實上權貴們也犯不上去招惹眾怒,因為請託的道路並沒有被孫丕揚徹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領導的吏部堵住了這條路,而吏部的考選只是官員升遷的途徑之一。另外還有一條途徑叫做保舉。為了彌補吏部考選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縣正官以上,都有權保舉官員。被保舉者的升遷調用不論年頭和資格,也不用抽籤。崇禎年間的刑科給事中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記載,曾有一個人求他保舉,開口就要送他三千兩銀子,由此可以想見保舉的行情。在保舉的道路上,權貴們的鄉里親舊僚屬門下絡繹不絕,從來就沒有斷過。這條溢洪道雖然不那麼乾淨,但也起到了穩固大堤的作用——權貴們可以繞開抽籤制度,無須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後幾年,崇禎皇上覺得抽籤選上來的官員實在不好用,又提倡保舉。第一批保舉出來的人果然不錯,但接下來便一塌糊塗了。經皇上的倡導,保舉的口子越開越大,請託方式也逐漸取代了抽籤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擠入撈一把的行列,於是形勢大壞。憂國憂民的人又呼籲恢復抽籤制度,卻發現這東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夢想。李自成破陝西,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這時吏部仍然在選官的過程中大肆收受賄賂。崇禎聽到了報告,就把祖宗牌位擺在朝廷上,讓官員們在神聖的氣氛中抽籤定崗。當時許多地方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有的地方危機四伏,險地和肥缺全在一個箱子裡裝著。崇禎規定,不管是什麼地方,一旦抽籤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員規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邊的人替他抽籤,不能讓他溜了。這就是說,在明朝滅亡前的最後關頭,抽籤制度再獲新生,而主持恢復這個制度的竟是勵精圖治、與朝廷共命運的崇禎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孫丕揚一樣讓步了。皇上有權,但是找不准打擊或提拔的對象,分不清敵我友,貪官污吏用資訊戰打敗了他。
抽籤當然不好,但考慮到這許多複雜情況,《明史》的作者最後還是說了許多體諒孫丕揚的話。這位史官前輩說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實實地轉述如下:孫丕揚創建掣籤法,雖然不能辨才任官,關鍵是制止了放任營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說不定情況更糟。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聖賢的話去責難他。
五
說了半天,官場上的各種關係都擺平了,大家都沒牢騷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繳了皇糧國稅,養了千千萬萬的文武官員,自然期望上邊派來一個賢能的領導,否則很應該大發牢騷。不過發牢騷也白髮,他們的嗓門不夠大,掌權者聽不見。這個比喻是嘉靖和萬曆年間著名的清官海瑞說的,原話是:「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於上。」海瑞這句話說得異常簡潔精確,後人很難超越。但是這話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可疑的前提:上邊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滿一定會替他們作主麼?事實上,大量的官辦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了官員的服務對象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這條信息通道並沒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戶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丟官,除非他們在官場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顯然不能得到歷史經驗的證實。老百姓的嗓門確實有問題,但是加害於人或者造福於人的實際能力更成問題。
這就是說,在進行官場謀劃,努力擺平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無須考慮老百姓的壓力,他們根本就不能構成一個壓力集團,甚至連一個輿論集團也不是,不過是一盤散沙。那時候又沒有「海選」的手段,難道某粒沙子還能跑到吏部去為你爭肥缺或者砸飯碗?如果不能,考慮他們豈不是多餘?
作為整個政權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論和原則上非常重要,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選賢任能」、「為民父母」、「愛民如子」之類的大原則和正式規則,以免洪水泛濫,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這一套,老百姓也會感到十分幸福,當牛作馬雖然免不了,皇親貴族的三宮六院和伺候他們的萬千宦官也要好好養活著伺候著,但身邊畢竟有了一個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歸,兢兢業業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節和數量掌握得比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暫時作穩了奴隸。
但是在現實的制度運作中,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無論是壓力還是牢騷,什麼也傳不上去,這就難免「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因此就培養出了敲詐勒索,勾引出了官場請託,豺狼餓虎們一個個地混進了牧人的隊伍,吃得牛羊們紛紛斷子絕孫,這便是最黑的潛規則。按照魯迅的比喻,這就進入了想作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位於白色的正式規則和黑色的潛規則之間。沿著這條灰色道路上來的放牧者則是個大雜燴,勤狗懶狗好人壞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趕上誰是誰。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的情況下,孫丕揚等有覺悟勇氣的好幹部,運籌帷幄,建立各種同盟,巧妙地動員官場上的各種力量,經過努力才給牛羊們爭取到這個政治成果。這個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稱之為成功,也可以稱之為失敗,這大概也是各朝代總能夠維持二百多年,最後卻終於難免滅亡的道理之一。
《炎黃春秋》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