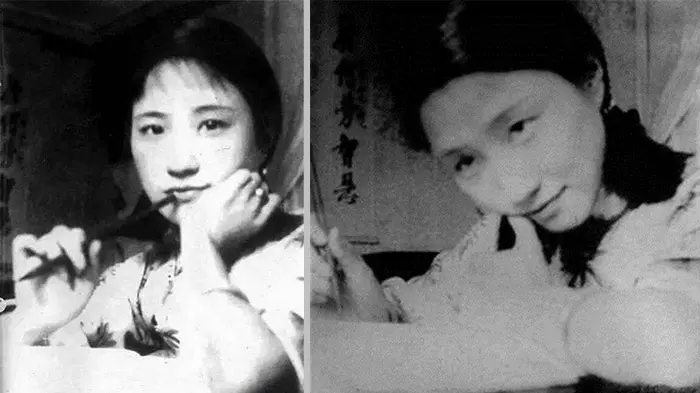
1955至1956年間,我在初中讀書時,我的繪畫師父錢方軾先生(曾任民國政府財政部鹽務總署署長,北京哈佛同學會會長)經中共中央統戰部批准從上海去美國與妻兒團聚,父親張羅著替我重找一位教畫的老師。我的金石篆刻師父陳巨來先生說,「我介紹你去跟小曼學學吧。」
父親和我喜出望外。父親是專治文學的。我也已經開始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小小年紀的我,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朱湘等的詩作已熟誦不少,對徐志摩陸小曼的愛情故事早從《志摩日記》、《愛眉小札》、《小曼日記》等書中知之甚詳。如今能有這樣的難得機會,我心中對第一次的拜見充滿了期待和想像。
巨來老師帶領我從他的富民路寓所走出,到延安中路拐彎,不幾分鐘,到了靜安公園對面的延安新村。那就是陸家的所在了。
陸小曼女士住在二樓。巨來老師一邊走上樓梯,一邊叫喚:「小曼,學生來了!」我聽得房中有答聲傳出,「請上來!」
那時,上海人家居處都不寬舒。陸小曼被安排在上海中國畫院當畫師,月工資八十元。所住是原來的舊居,樓下已是別姓人家。她的房間雖不算小,但會客,作畫,寢息均在其中。
室內光線不甚明亮,原來窗簾未拉開。時值四五月份,但一個鑄鐵火爐仍然燃著煤塊,一個已經沸滾的水壺,壺蓋一掀一掀地。火爐旁邊,蜷臥著一個慵懶的老貓。
陸小曼女士靠坐在一個大藤椅上,並未起身。陳老師向著尾隨在後的我招手:「來,向陸老師鞠躬!」
我略帶生怯地上前,站定,正面向陸,恭敬鞠了一躬,站直,再行第二躬時,陸老師開口了:「好了!可以了。」
我遲疑地舉頭看陳老師。他說:「再鞠兩個。」他對著陸老師說:「方晦拜我為師時三鞠躬。今天拜你,怎可只鞠一躬?」
陸老師笑著說:「你是大名家。我是三腳貓。拜你三鞠躬,拜我一鞠躬夠了!」
我思忖一下,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二躬。
陸老師說:「方晦,坐吧。坐吧。」她用著一種靜定的眼光注視著我。我知道這一注視會決定她對我的全部觀感和印象。我雖杌隉,但無懼色,因為陸老師的態度異常親切,她的語音里有著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她的眼神會掃除陌生來客的一切拘謹。
那時陸老師只不過五十歲出頭,但卻瘦弱蒼老,頰萎腮癟,口中只剩一二餘齒,跟我心目中的陸小曼女士的形象反差實在太大。十三四歲的我,頓時為歲月對人之磨蝕感到無比悲涼。但是,隨意問答閒談一會之後,那表象的視覺漸漸沖淡,那當年使得詩人志摩深為陶醉,使得胡適等一班眾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質和魅力,就在她的溫婉語音與和藹神情中漸顯漸現了。
陸老師對我說,她沒有收過徒弟,沒有教畫經驗,自己也不用功,畫得不好。你以後就常來玩玩,談談,看看我畫畫,做個朋友吧。當時我如何作答,已記不起來了,無非是一個勁兒地點頭接受而已。陳老師說:「我也只教了他一個鐘頭。教他怎樣篆稿,怎樣翻印到圖章上去,再怎樣刻。就這樣。接下來,就讓他看我刻圖章。陪我聊天。」
陳老師先行告辭。陸老師的表妹吳錦女士端來茶水和糖果。陸老師叫她「阿錦」,我就叫她「阿錦阿姨」。她自丈夫過世後一直住在陸家照顧表姐的生活起居,陸老師吸中華牌香菸,每支只吸一半,直立撳滅,排列在煙缸里,一式長短,纖毫無差。我詫異這些菸蒂為何這樣留著,後來才知,那後半支中華牌香菸將由阿錦阿姨繼續享用。
自此,我便成了陸老師的小朋友和家中常客。陸老師生性隨和,脾氣特好。寬厚仁恕是她的最大特點。她對任何來客一概歡迎,家中常有京劇戲友和國畫院同事以及文史館的各業人士來訪,倒也常常高朋滿座。那時,跟她一起生活的除了吳錦,還有同居多年的翁瑞午和翁在外私生的小女兒「毛毛頭」,(陸老師將其撫養在家視為己出)。另有一個名叫「桃桃」的女傭。「毛毛頭」的生母「小寶」常來訪視,翁的其它成年子女也來探望,吳錦在揚州讀書的一對雙胞胎兒子(比我大幾歲)也常來省親,因此,陸老師家也就時有濟濟一堂的熱鬧景象。三十年後的八十年代,見到郁達夫夫人王映霞女士記述陸小曼的文章稱,小曼對她說:「……翁瑞午另有新歡了,我又沒有生男育女,孤苦零仃,形單影隻,出門一個人,進門一個人,真是海一般的淒涼和孤獨……」覺得這段描述與我所見的事實大相逕庭。不禁深信某些回憶文章不免失實,僅將「想當然耳」的內容寫成親歷的見聞,實在是有負讀者的。
1959年某日,我去陸老師家,只見好些陌生人圍在一個小房間內,我擠進去一看,翁僵臥在床,眼睛瞪著,口不能言。我叫一聲「翁先生」,他似有反應,眼珠朝我略一轉動。這時,曼師在臥室里聞聲喚我了。她獨坐在大藤椅里,異常平靜地對我說:「翁先生不行了。你不要去看。」在她臉上,似乎並無什麼永別的悲痛之色。
翁瑞午推拿醫生出身,曾經官至海軍部軍需處長,雖屬常熟翁家大戶,卻不是翁同龢的嫡裔。1949年後無業在家,靠變賣舊藏書畫維持與陸老師的共同生活。他精於彈詞饒舌,並收徒授課。他告訴我,當時上海很有名氣的美麗女彈詞藝人張維楨是他的門生;對此,我將信將疑,但陳巨來老師與許多彈詞藝人亦有深廣交往,卻從未否定過這一說法,又似證實翁並未吹牛。那時翁已六十多歲,身材很高,骨瘦如柴,談興極濃,常常手舞足蹈地對我談古論今,甚至竟說:「人稱陸小曼是海陸空。指她的三個男人:第一個男人王賡是陸軍出身,我是海軍出身,徐志摩則死於空難。」對於這話出自他之口,我十分反感,回家告訴父親。父親說,這人非常無聊,你不要理他。但我如何能夠不理他呢?後來,陸老師私下也曾告誡我:「翁先生口無遮攔,胡說八道,你不要聽他的那一套。別受他的壞影響。」此後,我對翁就守著一條界限了。由此也知道,他實際上不是陸老師的傾心而相稱的伴侶,至少在那時已經不是。
陸老師對我,始終親切,但也嚴肅。我去上課,她必先饗以水果,糖食,閒聊一番後再言歸正傳。所謂教畫,也只是叫我在旁看她作畫,或擎筆在紙上作些勾勒皴染的示範,沒有系統的計劃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創作,更是興至揮毫,興盡擱筆,所以半途而廢的作品特別多。儘管她的畫作在數十年前即受到胡適、楊杏佛、劉海粟等人的讚揚,但她絕不自視為成熟的畫家。她對我說:「我從來沒有好好用功過。你不要臨摩我的東西。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學我,是學不到本領的。」但是,我所見她的《廬山飛瀑圖》以及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幾幅較大的杜詩意境作品(中國畫院的官方任務),確實堪稱不可多得的精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顯露出來的那種清純靈秀的神采與風姿,是許多技法嫻熟的職業畫家表現不出的。
由於我從小愛好文學,同時隨著漸漸長大,已開始留意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我與曼師的關係,不可能不由繪畫的師生轉化成談詩論文,密議時局的摯友。曼師一生中,對她影響最大、最令她念念不忘的當然唯有志摩一人而已。她談志摩(始終是個長不大的孩子,是真的,不是裝出來的),也談胡適(溫雅有禮,關愛他人的),聞一多(頭髮亂蓬蓬衣服髒兮兮的),沈從文(當過警察。曾在她與志摩的家裡住過),泰戈爾(慈愛得像上帝),孫大雨(非常自傲,但不狂妄);也談林徽音(高雅美麗,與志摩極其相配。當年梁思成也追求林,為了替林買桔子,梁騎摩托出門,車禍傷腿,林不忍離棄腿殘的梁,才舍志摩而取梁……這是陸老師當時的說法。時至今日,我明白事情遠遠不是她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她談丁玲(很有才氣。當年胡也頻出事,是她推動志摩去向邵洵美借錢,以資助沈從文陪伴丁玲潛逃)。有一次,她精神很好,又談志摩的詩,她即興用悅耳動聽的曲子吟唱志摩的名篇《沙揚娜拉》,使我對音韻聲律之於詩歌的詮釋有了特別深刻的領會。
1957年,《詩刊》雜誌創刊,登載了詩人陳夢家談及徐志摩的文章,這使她極為振奮。出版徐志摩全集的意願在她心底死灰復燃。但與有關人士通了幾次信後,方知當局對徐志摩的仇視仍極深刻,她不得不又斷了此念。
我還記得陸老師對發表在《詩刊》創刊號上馮至的一首詩讚不絕口,說:「這才是真正的詩!」但老實說,我雖尊敬馮至,但對那首除了節奏明顯、音韻鏗鏘、格律嚴謹之外沒有什麼動人意境的詩,實在感覺不到有什麼引人入勝之處。
後來,我羞怯地拿出一本我與兩位同窗朋友的三人詩作合集抄本請求陸老師題簽,她即刻用毛筆在封面上寫下秀麗工整的楷書「歲寒集一九五九年陸小曼題」。可惜的是五年之後的1964年9月,我與一批同學以「反革命集團」案被捕時,這本《歲寒集》與第二本《朝露集》第三本《契闊集》一起「落入了三道頭之流」之手,直到我們平反出獄乃至今日,那幾本詩集再也沒有歸還給我們。
陸小曼老師並非如世間普遍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流連舞榭歌台,耽於逸樂享受的風月女性。實際上她非常敏感,對所處時代的特質有深刻的認識。她關心時局,對日甚一日的思想禁錮十分憂懼,對文化被政治所扼殺更感到絕望。她認真地看報紙,看《參考消息》,關注著國際國內的大小政治動態,隨時跟我討論分析。她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方晦啊,這是一個不可隨便說話的時代。最最要緊的是,自己內心的想法,千萬不能公開亂講啊。」
1960年前後,消息傳來,胡適在台灣參選總統。陸老師告訴我,中央和上海統戰部的代表在這個骨節眼上突然頻頻來訪,請她吃飯,並轉彎抹角地問起與胡適的關係,交情;還暗示,不妨通過香港的熟友聯繫聯繫嘛。也不必一刀兩斷老死不相往來嘛。胡適是很有學問也很愛國的人嘛。等等。我並不理解這種動作的含義。曼師說,當局的統戰工作可謂無孔不入。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貼近親屬。胡當選還是不當選總統,我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們還是來找我了。這說明,他們不會放過任何可能吹風到那邊去的細小機會,以影響那邊政治人物對他們的感覺。
1949年以後,為了避禍,陸老師基本上足不出戶,息交絕遊。熟友來訪,只談京劇書畫,不涉國事。但是政治運動是逃不脫避不開的。反右運動之前,上海中國畫院內部舉辦一個畫師作品展覽。當時畫院的畫師無一不是上海乃至全國赫赫有名的大師級書畫金石藝術家。陳巨來老師把存錄自己歷年印章作品的一個長卷拿去展覽。起先,那長卷展開的是他1949年以後的作品。「毛澤東印」,「湘潭毛澤東印」,「朱德之印」,「故宮博物館珍藏之印」,「梅蘭芳印」等等,等等,已經夠風光夠顯赫了,但是他老人家還不過癮,在布置會場之後,又悄悄把那長卷拉開一段,於是,「蔣中正印」,「張學良印」,「程潛之印」,「張大千印」等「反動歷史」就暴露無遺了。結果,當然,陳老師被「揪出」。事情未完,「反右」開場,他的這一「現行反革命罪行」加上一連串的「反動言論」被痛批一陣之後,他便被押送勞動教養去也。陸小曼是陳巨來的三十年老友,同事,還是近鄰,過從密切,陸小曼不發言批判陳巨來是怎麼樣也「滑不過去的」。於是,幾年之後,陳老師「解教」(解除教養)歸來,他與陸老師遂成陌路,還有深怨。那時,我剛從(隨同父母流放的)西北荒漠回滬,覺得這兩位於我情同父母的師長竟被政治高壓弄成了「冤家」,心中極為難過。我對巨師說:「陸老師倘不批你,她自己也完蛋了。」他說:「怎麼可以為保護自己,犧牲朋友?」我說:「你在教養農場裡好幾年了,怎麼還沒懂那一套的厲害?誰能對抗政治運動?誰敢講義氣保護朋友?」他不做聲了。過了一會,他又說:「別人揭我批我不關痛癢。小曼揭發批判我,就像尖刀刺在心臟上。你不知道,她揭發我十八條!十八條哪!」我說:「不管多少條,你們私下說的話她揭發了嗎?別人不知道的事她揭發了嗎?」他想了一會,說:「那倒是沒有的。如果有,我恐怕槍斃加上活埋還不夠哩!」我說:「那就是了。她是假批判呀。」我又說:「陸老師一直很關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後,她總要問長問短,既問健康,又問心情。」他問:「陸老師還說過什麼?」我說:「她是明白人,不說廢話。她是記掛你的。」這時,陳老師淚花涌動,大叫:「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見她!」我與巨師走到曼師家裡,還在樓梯上,巨來老師就大聲叫嚷:「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冤枉你了!」他倆雖未抱頭痛哭,卻也冰釋前嫌,和好如初了。
1960年之後,曼師健康每況愈下。之前,她還能梳妝打扮一番,去畫院開會,步履尚算輕健,後來,可怕的氣喘發作頻仍,往往坐在床上,由阿錦阿姨在背後抱持著,伸直脖子,上氣不接下氣,喉間「嘔嘔」巨響,要大半小時方能平復,但已筋疲力盡,不復能言了。由於那要命的哮喘必須用「可的因」來抑制,而該藥又只有少數幾家醫院的住院部才有處方權,所以,自1960年後,曼師是居家日少,住院日多了。
1960年4月,我家繼父母先後被打成歷史反革命遭逮捕和開除公職之後,再次大難臨頭:被動員去西北沙漠開荒。我向陸老師告別。她除了淚眼汪汪之外,說不出一個字來。十八歲的我還未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也不認為會與小曼老師暌別長久。我驚異於她臉上的懼怖之色,覺得是病弱使她經受不起任何波折。兩年後我回到上海,有了使得曼師和巨師重歸於好的一幕。那時以為災難已經過去,往日的生活又會回來,至少我又回到兩位恩師身邊,雖然我在那期間已經永遠失去了慈父。
萬萬料想不到的是,儘管曼師千叮萬囑,我仍然不免以言賈禍。1964年9月,我與幾位常在一起暢敘的同學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而遭逮捕。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不判不放地「悶關」四年之後,於1968年的某日,在囚室里巧遇翻譯家、新月派詩人孫大雨教授。若干時日之後,大雨先生偷偷告訴我,兩年多前他路遇吳錦,知悉小曼已去世了。每當入晚,我只有躲在被窩裡無聲哭泣的份兒。
在監獄服刑十六年零三個月之後的1980年12月,我被上海市高級法院宣告撤銷「無期徒刑」的原判,改判「無罪釋放」。回滬後,我重訪曼師舊居,卻是不相識的人出來應門,一問三不知了。後來,我輾轉找到了年愈古稀的阿錦阿姨和曼師的侄女陸宗麟女士,知道當年我的被捕使曼師受到極大的打擊和刺激,她憂忿驚懼過度,時常哭泣,遂至不起。阿錦阿姨還說,「文革」中滬上公墓悉遭破壞,曼師的小小墓丘早被搗毀無遺,現在連祭祀一下和獻一束鮮花的所在也沒有了。
1988年,我與某友合作撰寫了三十萬字的《飛去的詩人--徐志摩傳記小說》,請歷劫生還、年愈八旬的孫大雨先生題寫了封面,由中國河南黃河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曼師生前的最大心願,她曾囑咐我協助她實現的心願。我與合作夥伴克服了種種阻難,終於完成了這一任務。
我在心裡用這本書來祭奠曼師的在天之靈。
2007年11月12日紐約



















